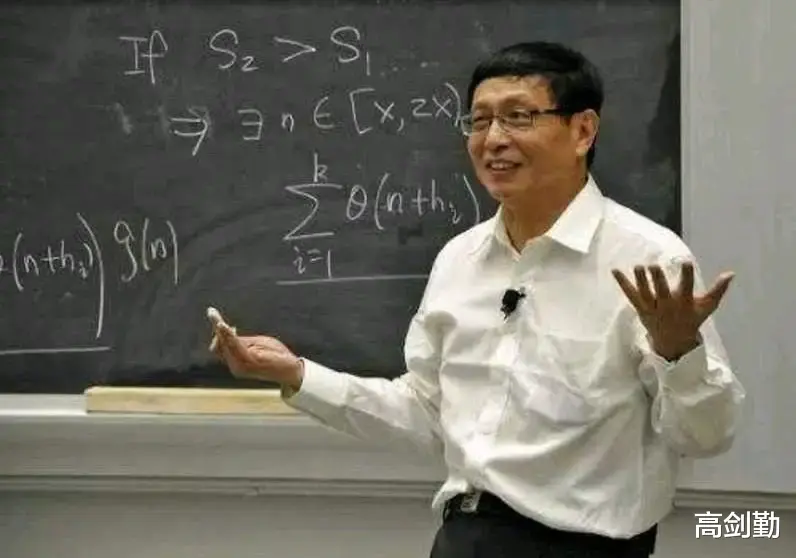彭练矛的“十年寒窗”,是在一次次搬家中度过的。
他的父亲是铁道兵。“修铁路要到处跑,哪里没有铁路,就到哪里修路。”全家跟着父亲辗转各地。1962年,彭练矛出生在江西鹰潭,很小就随父亲到了福建厦门,随后又去往福建南平顺昌县。
“我有很长一段记忆留在了顺昌的铁道兵部队大院里。一栋楼里上上下下的邻居,谁父亲从前线回来,总会带很多东西,比如小糖果之类,给每家的小孩都分一点。”在那里,彭练矛度过了一段童年时光。
彭练矛回忆说,当年就读的东方红小学建在一个山坡上,顺着一个大台阶爬上去就是顺昌一中,“我们大院距离学校大概五六里路,那时候觉得不算太远,一帮小孩成群结队地上学、放学,想着各种各样的法子玩。”
11岁时,他们全家来到了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一个叫虎什哈的镇子。每次搬家,彭练矛都会换一所新学校。“这么一倒腾,中间跑丢了几个学期。”
对他的同学来说,上学是件很奢侈的事。那时的农村,十几岁的孩子都要干活,有些孩子根本没有机会读书。
“连吃饱饭都是问题。”彭练矛有两个哥哥,三个男孩粮票都有定量,一个月只有十几斤粮食,没有油水,根本不够吃。为了填饱肚子,他们就拿粮食换红薯,一斤粮食差不多可以换7斤红薯。由于在福建时吃了太多红薯,吃“伤”了,彭练矛到现在都不怎么吃红薯。
在那个没有铁路、吃不饱饭的小镇,彭练矛考上了北京大学?。那是1978年,高考恢复的第二年,年仅16岁的彭练矛走进燕园,成为“文革”后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招收的首届学生。
上大学后,每月的粮票定量涨到了54斤,彭练矛终于能吃饱了。除了喂饱身体的粮食,更让他兴奋的是那些取之不尽的“精神食粮”,他总是早早地去图书馆排队借书,再“打游击”一样地找地方看书。
1982年,彭练矛考取了北大电子物理硕士研究生,此后又赴国外深造,开启了电子显微学和碳基纳米电子学研究的新篇章。
步入21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试图寻找能够替代硅的芯片材料,而碳纳米晶体管是最具前景的方向之一。从2000年至今,彭练矛坚守在国产碳基芯片研究一线,并首次制备出性能接近理论极限,栅长仅5纳米的碳纳米晶体管,成为国产碳芯片发展的领军人。
谈高考:“要读书就去最好的地方读”
新京报:你当年接受的小学、中学教育是什么样的?
彭练矛:那时正处于“文革”时期,科班出身的好老师很少,很多没经过正规教育,更不用说师范教育。学校教的不是数理化,而是“工农业生产知识”,包括拖拉机的构造、怎么制造沼气之类,更强调将知识应用于生产中,而不是死读书。
秋冬时节,河里水都干了,我们从生产队借手扶拖拉机,在河道里学着开。河道里风特别大,每次开完之后,回家就会生病。
新京报:在高考恢复前想过上大学吗?
彭练矛:那时没有高考制度,但大学还有其他选拔途径,比如名额分配到各单位,然后选拔推荐。我肯定想不到能上大学,因为我们家成分不太好,根本就没有机会上大学。
新京报: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是什么心情?
彭练矛:当时我的两个哥哥都在河北农村一个叫六道河的地方插队,恢复高考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他们离开那里的唯一途径,否则他们就要在那待一辈子。如果能考上,家里最发愁的事一下就可以解决了。而我当时还在上高中,高考对我来说没有对哥哥们那么特别。
新京报:当时高考竞争激烈吗?
彭练矛:高考刚恢复,积压了十来年的学生一起进考场,其中包括“老三届”,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高校能够容纳的学生也有限。我记得1978年、1979年的高考录取率大概只有6%。
新京报:当时高考考哪些科目?
彭练矛:得考七八门。数理化、语文、生物、地理、英文。英文分数是作为参考分,不纳入总成绩。英文我学了一点,但是没有信心能考好,所以没参加英文考试,我的英语参考分是0分。
新京报:你认为自己属于“天赋型”还是“努力型”?
彭练矛:1978年,我参加高考的时候,我的两个哥哥都考走了,就剩我自己在河北待着。我很努力地学习,也想跟哥哥们一样考上大学。
高考很难,但最难的不是学习,而是获取资料,因为只学“工农业生产知识”是不够的,必须去找数理化教材,但可能整个学校也没有一套完整教材。
那时,只要谁有以前的中学教材,我就想各种办法去借,或是用自己手里的资源和别人交换,然后用蜡纸手抄一份,习题也会抄写。我一直都是班里的好学生,老师拿到书或习题也会想着我。当时我自学了所有能够借到的教材,做完了所有习题。那时只有一个单纯的念头,就是把书读好。
新京报:当时在哪参加的高考?
彭练矛:要到滦平县城里高考。考试持续好几天,要提前去。那几天正好下大雨,路上都没法走车,比较危险。高考前夕的摸底考试,我的成绩在整个承德都特别好,铁道兵系统对我寄予了很大希望,后来部队专门派了一辆轨道车,把我和其他参加高考的同学直接送到了县城。轨道车有点像一节火车头,但不是用来拉列车,而是平时用于巡查和检查路况,只能装几个人。
部队管送不管接,考完试之后,我自己大概走了60多公里回家。还记得,路上要过河,河水都快漫到胸脯,那时胆子很大,直接就蹚过去了。
新京报:什么时候知道高考成绩?当时什么心情?
彭练矛:我的成绩在整个承德地区排第一。但当时没地方查成绩,县里先知道了消息,慢慢传到村里,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有一天,我的一个好朋友去邮局取信,看到一个写着我名字的信封,就顺便给我捎了回来。我老远就看见他蹦着跑过来,一看,是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特别高兴。
消息传出去后,学校的老师们也知道了,有的老师说:这娃可惜了,要是上“北大”多好,怎么最后上了“北京大学”?
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我去县里体检时碰到教育局的人,才真正确认了自己的分数。
新京报:能讲讲当初填报志愿的故事吗?
彭练矛:我们当时是高考前填报志愿。我所在的那个地方,有史以来没有人考上北大,你敢不敢报?如果报高了,风险很大。当时父母也不太明白怎么报志愿,很多老师都觉得我报高了。
我自己也谈不上特别有把握,那时想法特别简单,北大是当时全国最高学府,是我内心的憧憬,我就认定,要读书就去最好的学校读,所以就报了北大。
一开始,我特别想读数学专业。我很喜欢数学,但高考数学只考了80多分,物理考了95分左右,所以后来还是选了物理。当时看到有个专业叫“电子物理”,觉得又有电子、又有物理,看起来很厉害,就选了。后来才知道,电子物理不属于物理系,而是属于无线电系,无线电系是从物理系分出来的。
新京报:来北京求学是什么场景?
彭练矛:那时去上大学标配就是一床被子,叠成豆腐块,打个包,后面挂着洗脸盆和饭盆,还有一些书,背在身上就去了北京。
去上学之前,父亲送给我一块上海牌手表,当时算比较奢侈的礼物。我们家三个孩子,父亲给每人都送了一块表。那块表我一直戴着,毕业后去美国读书还一直戴着。有一回在学生食堂吃饭,天气比较热,就把表摘下来放在托盘里,吃完饭把托盘端去送洗,结果忘了拿手表。一出门就发现表没了,赶快跑回去找,但没能找回来。
新京报:在燕园的日子是怎么度过的?
彭练矛: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就拼命读书。老师们非常好,大一大二的时候有几个老师我们特别喜欢。
看到北大有这么好的图书馆,我们都去排队借书,有时一本书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借到。但当时要想找地方看会儿书可不容易。那时候图书馆学生多、位置少,拿着阅读卡才能有一个座位。阅读卡不是人手一张,我们1个宿舍7个人,只有1张阅读卡。当时图书馆规定,晚上7:00以后就可以随便坐,那时可以安心坐在那看书。教室也一样,什么时候教室空了,就跑过去待着看会儿书,什么时候有人来上课,再换个地方。
新京报:去图书馆喜欢借什么类型的书?
彭练矛:一类就是专业里头最“猛”的书,像《吉米多维奇数学分析习题集》、J.D.杰克逊的《经典电动力学》等,这些书得早早排队才有可能借到,而且看一个上午必须得还回去,然后再继续排队借;另一类是文学经典,虽然是理科生搞科研,文学名著也要读,像《约翰·克利斯朵夫》《三个火枪手》,一周要读好几本。
新京报:有人怀念80年代,你对那个年代有什么特殊的印象吗?
彭练矛:那时大家都意识到,我们和外面的世界有巨大差距,觉得国门打开了、有机会了,都想要提升自己,大家都生机勃勃,追求理想。我觉得,任何时候都应该这样。
谈当下:认真把事做好,才能把控自己的命运
新京报:几十年过去后,再回忆高考,有什么感触?
彭练矛:对我来说,高考谈不上改变命运,我一直觉得,这就是我该做的事。不管做什么,都要认真把事做好,这样才能够把控自己的命运。
新京报:如何看待当下的高考?
彭练矛:高考只是人生中的一道坎,人生中还有很多道坎。即使没有上大学,也不说明人生就不能出彩,认真做事,在什么地方都行。即便上了北大,有积极上进的,也有懈怠放松的。
新京报:与过去相比,现在的学生有什么不一样?
彭练矛:不太一样。当时我们的选择少,还是毕业分配的年代,所以显得单纯一些。同学们很纯粹,读书就是要提高自己。很少有人想着找工作的事情,想的都是读完之后怎么为国家服务。那时候也分成绩好的和稍微差一点的,但放松和放弃自己的人非常少。
现在的孩子视野比较广阔,想法也比较多。但很多学生没把精力都放在读书上,总想着如果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大部分孩子考研、读博是在逃避就业,真正热爱科研、想做学术的少了。
很多学生能考到北大,可以说是天之骄子,但有些同学经过一两年,觉得很难再处处保持最优秀,一旦接受了“我不是最好的”设定,对自己就降低了要求,开始琢磨“我能找个什么工作”“谁谁谁能挣多少钱”“哪个公司今年招几个人”这些事。
但我始终觉得,我们国家这么大,留给大家去创造、去做贡献的天地非常广阔,很多孩子生来是做大事的,而不是仅仅为了养家糊口。
新京报:又是一年高考时,你最想对今年的考生说些什么?
彭练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觉得这句话就特别好。
彭练矛,材料物理学家,主要从事碳基电子学领域研究。201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北京大学电子学院院长、北京大学碳基电子学研究中心主任。新京报记者冯琪摄影新京报记者浦峰编辑缪晨霞校对付春愔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