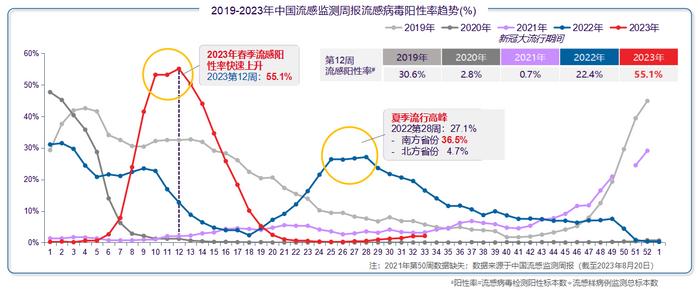文|于丽丽
编辑|刘旌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一天,在清水湾半岛的港科大,时任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刘应力陆续敲开很多实验室的大门。
此时的深圳正急于产业转型,但苦于没有好大学,好研究机构,就想出借鸡生蛋的一招:去拜访那些好学校的教授,让他们来深圳和企业一起做研究,借此走出一两家公司。
等敲到3126实验室大门时,开门的是一个难得的不会讲粤语、拖着一口湖南腔普通话的教授。
这位教授虽生于内地,但辗转中国香港任教,先后就读于卡耐基梅隆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是美国机器人领域的两所顶级学校,意味着他背后是一张庞大的机器人领域的产业版图。
这个人的名字后来广为人知:他就是港科大电机系教授,自动化技术中心创始人李泽湘。
这次敲门堪称中国最早的运动控制公司——固高科技故事的起点。不久后的1999年,深圳市政府与港科大以及北大联合成立深港产学研基地,而固高成为港科大的第一家入驻企业。24年后的2023年8月15日,固高科技登上创业板。
对教授李泽湘来说,成立固高是他从学界到产业界的关键一跃。长期以来,中国的高校与产业界存在严重的隔绝。而李泽湘和他的搭档——港科大教授、前工学院院长高秉强,以及港科大的老同事、长江商学院的副院长甘洁,共同打破了这个局面。
但有趣的是,在接受访谈时,李泽湘反复向“暗涌Waves”强调,很多人把他归为“科学家创业”的代表其实是一种误解。尽管固高是李泽湘体系的第一个IPO,但他更多时候扮演的其实是这个路线的“叛逆者”。
科学家创业道阻且长,李泽湘早就转向另一条道路:支持学生创业。
事实上,8月15日固高上市的那一天,他的微信朋友圈一片安静,转发内容与此毫无关系。似乎这是一场与他无关的IPO。
的确,李泽湘更大的名望来自于一份可以很长的公司名单:不仅包括课堂里孵化出的千亿市值大疆,还包括3126实验室里孵化出的李群自动化、逸动科技,以及位于松山湖的XbotPark机器人基地孵化出的云鲸智能、海柔创新等。在3126实验室呆过的百名硕博、博后及访问学者,最终打造了约50家颇具声誉的公司。2021年的一则数据显示:XbotPark机器人基地共孵化了超过60家公司,并从中走出了15%的独角兽或准独角兽,整个基地公司成活率80%。
从自己躬身入局到支持学生创业,背后是李泽湘对产业奥秘的一次洞悉。
“所谓科技成果转化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人的转化才是最重要的。”数月之前,李泽湘在接受“暗涌Waves”访谈时说,历史早已证明,“用技术积累去找应用是非常低效的,更高效的是用问题去牵引技术”。以色列的案例也早已提示,科技成果的转化最终依赖“人的流动”。
所以他要打造一个更大的、让人自由流动的体系。过去十年,除了XbotPark松山湖总部基地,李泽湘还在常州、宁波、重庆、深圳、香港基地向一群身处象牙塔的工科学生,系统化地搭建从创业方法指导到供应链、资金支持的全方位创业生态支撑体系。2022年,他又发起成立XbotPark广州基地(即大湾区国创中心智能系统创新基地),开拓产学研一体化发展的进一步探索。
这条道路同样漫长,但这也是讲述李泽湘的意义:在中国重塑产业格局的当下,他的故事恰好揭示出了产业变革真正的水下力量,以及他们正在面临的围困与阻碍。
李泽湘会获得更大范围的成功吗?
好像还为时尚早。但他的学生、李群自动化创始人石金博说,“他在平静的水里丢了一个石子,至少水变化了。”无论如何,她希望李泽湘能有足够的资源去试错,“就让他的子弹多飞一会”,因为“他跑得比谁都快。”
一堂课的奥秘
2019年,五源资本董事总经理陈哲第一次见到海柔创新的创始人陈宇奇。
让他印象颇深的是,尽管当时整个海柔状态平平:没啥收入,业务刚刚起步,整个公司命悬一线,但陈宇奇整个人“极其骄傲”。面对抛来的问题,陈宇奇单刀直入地表示:“我用四年只做了一款产品。”
在陈哲看来,海柔的产品“不同于国内一股脑抄袭海外Kiva的方案,无论原理还是结构上,设计都非常创新,但因为工程上难点比较多,之前从未有人成功落地过。”
同样是2019年,源码资本合伙人常凯斯在抖音上刷到了一款云鲸智能的产品,研究后发现“这完全是从第一性原理出发的自主创新,而不是模仿国外的微创新。”
海柔和云鲸都是早期入驻XbotPark机器人基地的初创企业。某种程度上,这两位创始人对于产品的执念——甚至在一些人看来是不切实际的执念,都是典型的李泽湘偏爱的创始人画像。
这也让人联想到李泽湘的成名作:在课堂上发现的大疆汪滔。
在一起参与了大疆投资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前工学院院长高秉强看来,汪滔的发现更多是“一种偶然”,但他的成功,给了李泽湘发现更多汪滔的“独特手感”。
而这种独特的手感,其实很多来源于一个独特的比赛。
关于这个比赛,一个更早的典故是,2014年,当红杉资本创始合伙人MichaelMoritz飞往深圳,问汪滔有什么可以帮忙时,汪滔始料未及地提出,希望后者帮忙办一场全球机器人大赛,因为他自己曾两次参加并极大受益于它。
这个名为Robocon的机器人大赛背后正是李泽湘选人的奥秘。
通常来说,Robocon的比赛规则是:10个月内完成几款机器人的研发。不同专业的学生组成一个团队,包括机械、电子、计算机等领域;操作上,则需要有进度、项目管理、后勤、宣传等方面的协调。
这套规则恰好相当于完成了一次小型的创业试炼:“目标明确、资源有限、时间有限、方法不唯一”,从而可以筛选出那些有创业者天赋和体质的人。
事实上,从亚太机器人大赛选手里,也走出了北京极智嘉(物流机器人)、纳恩博(平衡车)、深圳朗驰(巡检机器人)、普渡科技(送餐机器人)、松灵机器人(承载机器人)、因时机器人(直线驱动器)、灵动科技(机器视觉)等几乎中国机器人行业的半壁江山。
这场比赛也让李泽湘研制出了一门与之匹配的课程:一门机器人的比赛与设计课。这门课大疆汪滔上了两次。2004年、2005年两届,汪滔分别斩获Robocon香港地区冠军和国际赛季军。而在此过程中,他主导开发了直升机飞行控制系统——这后来成为了大疆的基石。
这门和比赛规则设置相仿的课程,是典型的“项目制”教学模式,且完美契合了新工科教育的三个新特点:学科交叉、动手能力、供应链管理。
在奇诺动力创始人梁哲看来,Robocon以及这堂课最重要的价值,其实是改变了对学生的一个评价体系,它让动手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超越了习以为常的所谓学分或者发paper论。
在李泽湘的学生、逸动科技联合创始人万小康回忆中,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李泽湘招学生,也会按照名校、高分等原则,但做固高以及Robocon比赛之后,他的招人标准开始变化。
从2006年开始,李泽湘陆续从各高校Robocon机器人队招收了很多学生。
因为洞悉到Robocon的神奇,后来的李泽湘也尝试着把这门课做成一个产品。2014到2018年,李泽湘结合自己在机器人领域的培育和孵化经验,逐渐探索出一套基于项目制学习的课程模式,并通过去麻省理工、斯坦福、欧林工学院等美国做工程教育颇成功的学校调研交流,把这套方法论逐渐打磨完善。
在把设计思维、工程思维、系统思维等创新核心内容一起整合后,又通过一次次在XbotPark基地开课迭代将之本土化,最后形成各种不同周期的硬科技创业营产品体系。
这些产品通过不同轮转,既可以帮助初入基地孵化的学员,学着去定义产品和整合供应链,又可以作为一种“拉长的面试”,帮李泽湘筛选到最适宜的人。
2015年,25岁的上海交大研究生张峻彬通过给李泽湘写信自荐,作为第一个被引入的创业者,来到位于松山湖的XbotPark机器人基地。
在一个曾在基地做过多年运营的人看来,张峻彬完全符合李泽湘定义的创业者画像:初出校门的年轻人;有团队管理视角,有allin精神;最好干过机器人比赛这种硬仗。
最佳的位置
大疆之外,李泽湘同期还参与过另一个学生创业项目:比锐精密公司。只是最后以失败告终。
这是一家半导体封装设备领域的初创公司。在很多人的讲述中,它也是李泽湘为之投入了大量热忱的公司,但最终结果让他有所反思和总结:项目一定要由跑在前面的学生主导,而且很多时候放手不管,可能发展得更好。
从最早做固高时需要去买一本哈佛的教材《如何开始创业》,到不同程度地参与大疆和比锐,李泽湘一直在探索一个工科教授,应该如何参与创业和创新。这也是许多人对所谓“教师创业”的诘问。
当“暗涌Waves”问李泽湘的学生创始人们,“李老师会插手具体公司事务吗?”他们都会飞快地回答,“不会。”
早在港科大时,3126实验室与其他实验室不同的是,李泽湘很少指定“你做什么”,他会问:“你想做什么”。
深圳科创学院是李泽湘一次新的尝试。它会与高校合作,吸纳有潜力但没有团队、点子和资源的“三无”年轻人到学院,帮助他们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创办硬科技企业。
深圳科创学院副院长于盈,原来在凤凰卫视主持一档探讨未来科技教育发展的节目,后来作为1号员工被李泽湘拉来搭建深圳科创学院。前期筹备有很多决定要做,李泽湘又总是飞来飞去。有一次,她攒了10个要决定的事,准备和李泽湘一起碰碰。结果,李泽湘笑笑,只给了她一句:每天都有这么多的决定等着你去做,你不感觉自己很幸福吗?
在李泽湘的学生看来,当遇到难题,李老师肯定不是你试图获取最佳共情的对象,因为他给你的答案永远是:这是你的问题,你自己去决定,你得自己决定。
一位做过很多科学家创业孵化的投资人告诉“暗涌Waves”,很多科学家的创业失败,都在于他们很难克服过大的自我ego和掌控欲,而李泽湘显然更早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把李泽湘的角色更多定义为“麦田守望者”,而这种角色往往可以给创新提供最有效的庇护。李泽湘的孵化是放养式的,因为他确信:“没有培养起来的企业家,把你育成苗,你要自己长大”。
寻找到一个教授的最佳位置后,让李泽湘获得更高胜算的原因还在于——按照一句流行语来说即:坚持难而正确的道路。
和李泽湘一起参与了很多投资的长江商学院副院长甘洁告诉“暗涌Waves”,在跑遍深圳几十家孵化器后,她觉得,李泽湘的奥秘还包括,从2014年建松山湖基地开始,他就重视原创技术,“这是他和其他人的最大区别。”
在硬件创业这样一个链条复杂、周期漫长的重模式领域,以及中国这样一个容易同质化竞争、讲究资源和经验的人情社会,这无异于一个大胆甚至天真的实验。
李泽湘对于原创的自信最初来自于大疆。
有一次,李泽湘和一起参与大疆投资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前工学院院长高秉强以及汪滔在深圳一个餐馆一起吃饭。席间,高秉强不无感慨地说:“再过几十年,回望中国科技企业史,会发现大疆是一个分水岭”,因为它最早证明了“中国的年轻人可以做出世界级的产品和科技超前的公司。”
这背后其实还有李泽湘对另一重残酷真相的发现:尽管大湾区在历经代工、山寨时代后建立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制造业供应链体系,但因为没有自己的品牌,就只能赚取尾部的利润。像手机,苹果公司赚了60%利润,而中国的代工企业只占2%不到。所以早在2014年,他就试图带领一群年轻人用“原创式创新”改变这种局面,去赚取产业链更顶端的定义产品的钱。
但年轻人的劣势也很明显。当时整个创投圈都还在经历移动互联网红利的最后疯狂,位于舞台中央的,是种种可以快速起规模的互联网项目以及大公司出来的成熟创业者。偶尔有投资人进来看一圈,看到一群学生创业者,和他们埋头做的一些小家电类、硬件类产品,最后冒出的评价往往是:真的靠谱吗?
2018年底是云鲸最重要的一次投资。当时产品还没全出来,张峻彬频繁飞北京,见了大概二三十家投资机构,但没多少人搭理。一个当时见过张峻彬的投资人,形容当时的张峻彬“背个书包”,“很内向”,这让他非常犹疑。
为解决融资困难,李泽湘和高秉强、甘洁成立了清水湾创投基金。如果项目立项,就可以获得一笔经费进入探索期,如果走到天使轮,则可以获得200-500万左右的经费。
2018年底云鲸那一轮融资中,有家机构最后跳了一半票。李泽湘就站出来,补了这一半。
而上述犹疑的投资人,后来想到当年见张一鸣时,也曾误判为“一个不像成大事的程序员”,于是回头去追,但云鲸已投不进去了。
之后,云鲸在2019年到2021年短短三年内,完成了从A轮到E轮五轮融资。
同时,在一年完成三轮融资的,是估值从3亿人民币升至20亿美金的仓储物流机器人海柔创新。
一个手电筒,一个打狗棍
带领一群初出校门的年轻人打天下无疑风险重重,所以李泽湘也构建了一个庞大的系统来对抗这种脆弱。
在一位曾在基地工作的运营人员看来,李泽湘这个系统“是一个闭环的topdown(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它很好地抓住了硬件创业三个核心要素:“产品定义、供应链和人”,而且每一项都有对应的可落地产品。
在东莞松山湖旧基地的6公里处,李泽湘新建了一个占地6万多平米、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可以容纳100多个创业团队的XbotPark机器人基地总部园区。这是他用早期赚的钱置换出的,可以庇护年轻人做硬件创业的理想之地。
这里几乎集合了硬科技创业所需的所有要素,不仅包括中试车间、电子实验室、3D打印实验室等设施设备,还包括幼儿园、图书馆等很多生活配套设施。
关于产品定义,在李泽湘看来,最需要完成的是一些思维转换。比如设计思维是去发现机会与问题,工程思维则是用技术把东西做出来并且快速迭代,商业思维是去判断如何切入,如何系统闭环,并产生现金流、利润,最后则需要用有勇气和胆量的创业思维整合起来。
一个在基地工作过的运营人员告诉“暗涌Waves”,初入XbotPark基地的公司,除了硬科技创业营的一些基本训练,最初还会有相关老师和项目经理去频繁交互,去矫正一些过去应试教育下的一些思维习惯,比如只会解决问题,不会定义问题。比如做用户调研时,不是乱访谈,不是自嗨,这样才能确保后续产品定义的整个大方向是对的。
机器人行业的本质是制造业。也正因此,供应链整合能力就变得不可或缺。
在FA势能资本创始人黄俊看来,供应链本质是“一种信任”。一家大公司可以靠量来获得信任,而小公司则不然。上述运营人员告诉我们,机器人基地的初创公司在供应链上遭遇的困难可以称之为“门当户不对”。
大湾区有非常成熟的供应链,但这仅局限于大批量生产,对早期团队来说,一个更常见的现实是:很少有公司会接中小批量生产,即便接了,质量问题往往很大,整一批都可能报废。而且不同阶段,要匹配不同供应商,这对初创公司来说,消耗的心神就非常大。
基地拆解供应链难题的方法,是建立供应商提前分级筛选的数据库,同时也会把基地创业团队们“打包”成一个整体的B级客户,去和大的供应商对接。
考虑到每家公司需求不是标准化的,李泽湘在总部园区的规划中,也特意建设了10000平方米的地下工厂和12000平方米的可以解决小批量、多种类问题的共享工厂。
如何让这套体系持续运转?不仅源于持续进化的设置,也来自于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比如耐心。云鲸产品开发到第三年,有的投资人开始沉不住来催,这时,李泽湘来工厂看产品,问产品怎么样了。张峻彬说还差点。李泽湘直接说”差一点,就别发布了”。
比如接纳失败。基地有家名为恩茁的农业科技公司,之前因为一些政策变化,团队被迫解散。李泽湘就问创始人还想不想做,想做就又给了他一笔钱,后来整个团队又重组起来。
李群自动化石金博说,李泽湘对蛰伏期的耐心来自他能看到创业者在财务报表之外的成长,而很多投资人如果没有经过产业训练,就会心慌。
而在逸动科技联合创始人万小康看来,相比在人力、供应链等现实层面的协作,李泽湘打造的这个体系更大意义是,它是一种精神共同体。
XbotPark早期经常开创业者大会,在很多人看来,其实就是比惨大会。经常这边一个人讲完50张ppt,说“四个创始人,现在只剩我了”,下一个则是“公司只剩俩人了”。
在一次采访中,李泽湘表示科技创业就像走夜路,“一个人会很害怕,两三个人或三五个人一起,再给你一个手电筒,一个打狗棍,就不害怕了。”
创新者的窘境
有一次,李泽湘和理想汽车的创始人李想聊天。聊到深夜,俩人最后的一声长叹是:为什么4000个中国工程师可能不敌300个特斯拉工程师?
答案当然有,是系统化、工程化能力的问题。但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教育的问题。
在把松山湖总部基地的模式复制到全国多地后,李泽湘发现好的创业者和项目并没有那么多,而所有体系内的公司几乎都面临人才之困。
其实,早在做固高时,李泽湘就遭遇过人才荒。当时的学生一毕业就去了美国,于是他在2004年在哈工大深圳研究院创立了自动化学科部,开始按港科大的模式培养学生,希望他们在未来的关键时刻顶上用场。后来在大疆成立的早期,这些学生果然成了骨干成员。
大疆的标杆意义让李泽湘接续了这些教改实验,在有更大影响力加持后,他尝试用孵化独角兽的产业需求,倒推新工科教育改革。过去几年间,李泽湘以松山湖等六个基地为圆心,和周边的很多大学都展开了新工科教育和科创教育的合作尝试,从开设新课程,到合作试点班,再到做联合学院,但这些项目中很多都进展缓慢。
某种意义上,这是先行者的困境。一个参与过前期推广的运营人员告诉“暗涌Waves”,这件事落地难度,在于你需要顶层(地方政府和学校)到中层(院长、教务处处长)到底层(老师)都有人支持。但现实是,这里每个人都身兼好几个角色任务,而科创不是最主要的那一个。
比如对高校来说,最大的驱动力往往来自科创比赛拿奖,或者和成熟企业合作获得直接利益,而不是新的教学模式实验。对老师们来说,他们的评价体系往往还是paper和经费。很多跨越到商业的高校老师甚至会被同行认为是去赚钱,“变脏了”。
“产学研”是一个被喊了很多年的口号,但其中通道依然诸多梗阻。
深圳科创学院于盈在跑遍二十多所国内高校的“双创学院”、产业园后发现,以参加比赛拿奖为目的的项目往往很难跑出来,这些项目通常都是导师选择的方向或拥有的技术,商业模式基本是ToB或ToG,年轻人没有动力也没有资源做商业落地。
商业价值的缺失,很大一部分在于学校到底是一个封闭体系。一个在美国学习、工作过多年的创业者告诉我们,在美国——尤其加州附近的一些学校,学校和产业之间的流动非常频繁。很多老师发现一个好的创业方向就可以去开公司,“之后即便做垮了,还可以回来教书”。
固高科技,某种意义上就是这样一种“流动性”的胜利。当时的香港科技大学,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的基础上,制定了产业转移的政策,允许老师每周可以有一天时间在外面做咨询,做专业活动。
新工科教育的推广同样困难重重,因为它在挑战一种集体惯性。尤其是随着涉及人群范围的扩大,这个体系会需要更多的资源、人力,甚至一个全新的评价体系。
即便在美国,尽管欧林工学院做了20年,很多毕业生薪酬都超过了麻省理工和斯坦福,但它依然是一个小而美的学院:只有300多位本科生,没有研究生,而且只限定在工程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以及机械工程三个学位,很难被大规模复制。
也因此,他的一个学生对“暗涌Waves”说,比起做一所综合型大学,李泽湘可能更适合聚焦在欧林工学院这种模式的学校,用他在机器人领域的洞察和积累,去培养更崭新的力量。
“体制外爱国者”
1978年,美国铝业公司访问中国,临走时提出给中国两个大学生奖学金名额。在中南矿冶学院读大一的李泽湘幸运入选。
这是一个来自湖南的乡下小孩眩晕的开始: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坐汽车,第一次坐飞机。到了洛杉矶,看见灯火通明,仿若外星球。
到了美国,李泽湘被巨大差距冲击。作为国家的代表,上课听不懂,东西做不出,重压之下,他几乎崩溃。
这时,他寄宿的美国家庭的男主人救了他,教他学会跑步。他就每天每天跑,雪地也不放过。“跑着跑着,人就走出来了。”
在匹兹堡的卡耐基梅隆大学留学时,一次上一门课,老师要求学生去一个十字路口呆三个小时,回来写报告。李泽湘当时在十字路口傻傻坐着,心想是该数行人还是数车辆,这种课程成为他的弱势。后来才知道,这种学习就是设计思维——通过观察和思考去发现问题的思维训练。
后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学会了批判性思维和数学工具。在麻省理工做博士后,则看到了做工程的全过程。所以对李泽湘来说,做教育改革,并非他在大疆之后的突发奇想。
早在1986年,在美国伯克利读完硕士的李泽湘,看到中美科技的差异,就和很多留学生一起编写过一份关于高校改革的建议书发到教育部。
2010年在南科大教改事件中,校长朱清时上任不久,香港科技大学自动化中心主任李泽湘就主动请缨成为建校团队一员,后来又把另外两个同事拉进来。当时,他对媒体说,他们三个人是内地出去读书的,所以有“一代人的高教改革梦”。
但2011年,因为种种意见分歧,三位老师决定退出。
一切看似中断时,大疆的成功又把这一切接续起来。大疆让李泽湘确信中国的年轻人完全可以做出世界级的产品和公司。
因为早期的积累,李泽湘也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但这并没有改变他什么。
无论走到哪,他还是穿得像个老师傅,到哪都背个旧的、磨损严重的暗红书包,习惯自己开车。
爬山是李泽湘最热衷的爱好。他带学生爬、爬山中接受采访,甚至用爬山来面试人。3126实验室因此一度被称为清水湾体校,松山湖基地则被称为松山湖体校。
爬山是他心性的某种映射。“走,我带你们抄近路。”当他说出这句话时,他的学生知道,大概率踏上的是“一条恐怖至极的野路”。
松山湖基地的一家早期创业团队的创始人对“暗涌Waves”说,有一年,李泽湘和他去美国,偶然发现在西雅图有个高山,就决定去爬。他们毫无准备,李泽湘甚至还穿着西装皮鞋。车开到山上时,上面在下雪,其他人多少有些犹豫,李泽湘却眨眼没了踪影。“一般做科研的教授都会很谨慎,怕风险,不会像他”。
在甘洁看来,大多数教授做的工作,其实离实际特别远,但因为这是自己安身立命的东西,大多数人会沿着既有路线走下去,而李泽湘则是主动打破这种局面,不走寻常路的那一个。
2021的60岁生日聚会上,李泽湘这样总结了20岁后的人生:30岁前,搞清了学术这件事;40岁前,搞清了教学这件事;50岁前搞清了创业这件事;60岁前,搞清了创新这件事。
关于他的这种家国情怀源自何处,他的学生倾向于归为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认为他是“最大的体制外爱国者”。而在李泽湘自己看来,对于一个成长中有过饥饿记忆的人来说,这就像一种本能。“就像逃荒的人,跋涉了很久,突然看见前面有片肥沃的土地”,“你怎么办?你不会躺着,不会歇着”,而是“去把它开发了,种植了,为下一次饥荒准备。”
他的学生、逸动科技的万小康觉得,这种反馈也可能来自于李泽湘曾受过恩惠。
2011年,万小康在泰国打机器人比赛。结果输了,中国五连冠丢了,他在泰国哭得一塌糊涂,李泽湘当时安慰他。10年后,在全国大赛现场,看到哈工大队长因为输了哭,万小康又去安慰他,把李泽湘当年对他所说的重新说了一遍。
他的印象里,李泽湘也提及很多这种恩惠。有一次当时去往美国的航班上,有个华侨看到李泽湘连个手表也没有,硬是摘下来送给他,后来又请他吃饭,帮他融入美国生活。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一些循环。”万小康说。
(感谢36氪作者苏建勋对本文的贡献。)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