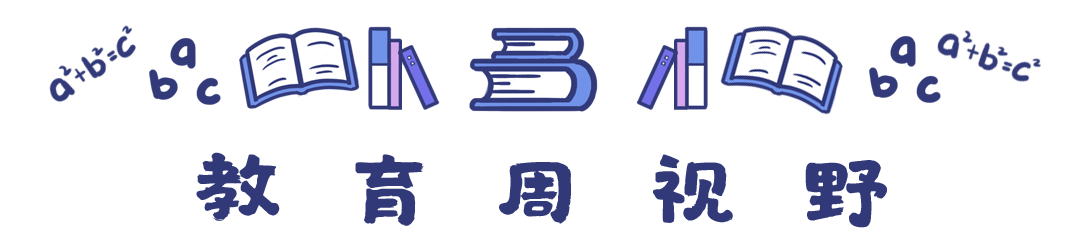学生妈妈用摩托车接黄灯到家里。
《我的二本学生2:去家访》
黄灯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4年2月
在2018年写作《我的二本学生》的前一年,大学教授、作家黄灯就开始走下讲台,跟随学生回家的路线,一路换乘高铁、长途客车、电动车、摩托车,来到腾冲、郁南、阳春、台山、怀宁、孝感等地,遇见了学生的父母、祖父祖母、兄弟姐妹、发小,在已经废弃的小学操场、老房子的屋顶、茶园的高坡、快递分装车间等地展开了家访,进入了“具体而稠密的日常生活”。
近五年的走访,凝聚成了这本新作《我的二本学生2:去家访》。黄灯更真切地看到,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一代,是如何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家庭的支持走进大学校园,而她触碰到一个更真实而丰富的中国,那些散落在地图上的小城、乡镇、村落里的父老乡亲,构成了二本学生背后的“教育资源”。
2016年,一篇火爆全网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让黄灯开始进入公众视野。2018年,《我的二本学生》一纸风行,再一次让黄灯成为中国非虚构写作的代表性作家。本期“名家有约”专访黄灯,一窥她走向讲台背后的本心与动力,以及历时五年的家访之旅。
●南方日报记者戴雪晴刘炜茗
“讲台之上”和“讲台背后”
南方日报:《去家访》的创作契机是怎样的?
黄灯:自2017年起,我开始到学生的故乡进行家访。《我的二本学生》则在2018年开始动笔,当时我就萌生了把家访内容纳入“二本学生”写作计划的想法。
对我来说,如果仅仅作为老师,去描述我从讲台上观察到的学生的样子,远远不够。这种表达是单向的,我应该走向讲台的背面,去了解他们为何会成为他们。可当完成《我的二本学生》后,我发现它的内容已自成一体,便先出了第一本。后来随着家访次数的增多,这部分的内容更加充实,于是创作第二本的时机也到了。
如果说《我的二本学生》是我在讲台视角的教学札记,那么,《去家访》是我走下讲台,走进学生家庭的考察和访问笔记。我想叙述和描绘出“讲台之上”和“讲台背后”的双重教育图景。
南方日报:学生的成长跟他们的故土、原生家庭、成长背景密不可分,你在家访的过程中,是否加深了这种感觉?
黄灯:的确如此。大学老师往往看到的是学生长成后的样子,如果把受教育的过程比喻成一条流水线,那么这些学生就像是已经制造出来的“产品”,快递到了大学老师手中。而他们从幼儿园、小学读到初中、高中,这一路是怎么成长的,他们的“产地”有怎样的风景?
所以在研究二本学生这一群体时,我选择回到现场和本源,探访他们出发的地方。我见到了他们的父母、祖辈、兄弟姐妹,甚至重走了他们上学时走过的路,这样我才能感知学校以外的更多维度,捕捉更多真实细节,内心也就更踏实。
南方日报:这些学生的父母和你是大致的同龄人,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成长于八九十年代,这是中国社会飞速发展的阶段。在家访的时候,你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什么?
黄灯:其实在出发之前,我就带着一个强烈的问号——我的同龄人把孩子送进了我的课堂,他们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我以前有个观点,认为“70后”这一代算是既得利益者,享受到了许多时代红利。当走进学生家里,我感受到,能够改变自身命运、切身感受到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人只有一小部分,大量没有机会上大学,还留在农村或出门务工的60后、70后,我想去看看他们的生活状态。事实上,在我家访的过程中,他们仍然无法停下手中的活计,我们难得的聊天机会,更多只能在铡猪草、煮猪食、织渔网、拣快递等间隙中进行。
南方日报:家访的过程,让你对学生的成长和生活轨迹有什么更深的感受吗?
黄灯:在大城市生活的人,可能觉得考上二本学校并没有那么难。可当我的家访一步步深入,会发现学生考上二本,其实已经是非常小的概率,需要他们自身的全力以赴和家庭的倾力托举。他们在求学途中经历的事情,远比我想象的更复杂更艰辛,往往要挺过一重又一重的关卡,才能叩开大学的门。
二本学生大多来自县中,可以说他们才是中国教育的底色。有个从广东某县一中毕业的学生告诉我,他那届共有一千六百多位考生,后来只有二十几位考上了本科。这个比例让我非常惊讶。学生们很重视上大学的机会,有个学生至今还留着高中时用过的两百多支笔芯,我在她家看到时感到非常震撼,那些笔芯,就像是她的勋章。
另外,我一直关注着学生们毕业后的去向,绝大部分留在大城市打拼,也有少部分回了家乡。2014年,有位学生回到了云南腾冲,我当时对此感到很疑惑,毕竟他在大城市里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当时他要在广州找到好工作,并没有难度。直到这位同学毕业三年后,邀请我去了他的家乡。我由此了解到他的父母以及背后的故事,才真正明白他当年的选择。而且,我很开心地看到,读大学的经历对他的为人处世产生了积极影响,他的价值观会更坚定。与单纯的生意人不同,他和客户聊的很多是文化、艺术、历史等话题,而不是只讲产品。这是大学教育给他带来的潜移默化的改变。
我对学生的关注,没有终点
南方日报:一般来说,家境不太好的学生,可能不想让老师看到这一面。你在家访中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黄灯:愿意受访的学生都已经过了心理的关卡,也有一些学生拒绝了我。虽然家访的时间跨度长达五六年,但我比较随机,并没有特意去挑选出“典型”的家庭。这些学生来自天南海北,成长背景也存在很大的区别。一旦走进他们的家,我能看到更广袤的中国大地。
例如,有两位广东同学的妈妈都是四川人,我想起90年代的一个镜头——南下打工的“川军”沿着长江的航线,从重庆坐船到岳阳的城陵矶码头,再浩浩荡荡地从码头走到岳阳火车站,坐列车来到广东。当时我还在岳阳读书,只是记得有这样一个场景,可当我进行家访时,突然会想起来,当年南下的打工人,有些就是今天我学生的家长。换句话说,在家访中所观察的细节,与我记忆中的一些镜头相重叠,我其实应该把这些细节写下来。
南方日报:从《我的二本学生》到《去家访》,我的一个真切感受,一是你的平视角度,二是真诚,你不是为做某个课题或者为写书积累素材。有个说法是,每个作家其实都是在写自己。你怎么看待这个说法?
黄灯:他们都是我的学生,我对他们有情感,所以“平视”对我来说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对学生有情感”和“把他们当作研究样本”是不同的。学者做这方面的田野调查时,往往会带着理论研究者、政策建议者的视角,而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我的学生是怎样的,我对他们家庭的观察是怎样的。
我的愿望,是通过书写与教育实践,尽力发现和寻找如何帮助学生安放身心的途径。在绩优主义横行的时代,我们应该心平气和地回到教育本身,让“人”的概念和声音得以强化和彰显。
至于说到真诚,我很认同“每个作家都是在写自己”。我自己就是县中的孩子,写学生就是写自己。我很庆幸能收获许多信任。有一回家访,我和一个女生挤在一张逼仄小床上,她跟我说,她很久没和像妈妈一样的人一起睡觉了,后来她从一个旧柜子里拖出一个箱子,把所有的奖状都铺开,让我看到了她每一步是如何抵达的,这让我非常感动。
南方日报:2005年你开始任教到今天,你的写作计划实际持续了近20年。接下来还有写作计划吗?
黄灯:在北京做活动的时候,白岩松第一个问题就是问我,你还会写第三本吗?最近也有不少朋友鼓励我继续写下去,关注这些学生当了父母以后,他们的家庭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只能说,我对学生、对年轻人的关注,没有终点。如果有机会,我还是会继续写下去。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