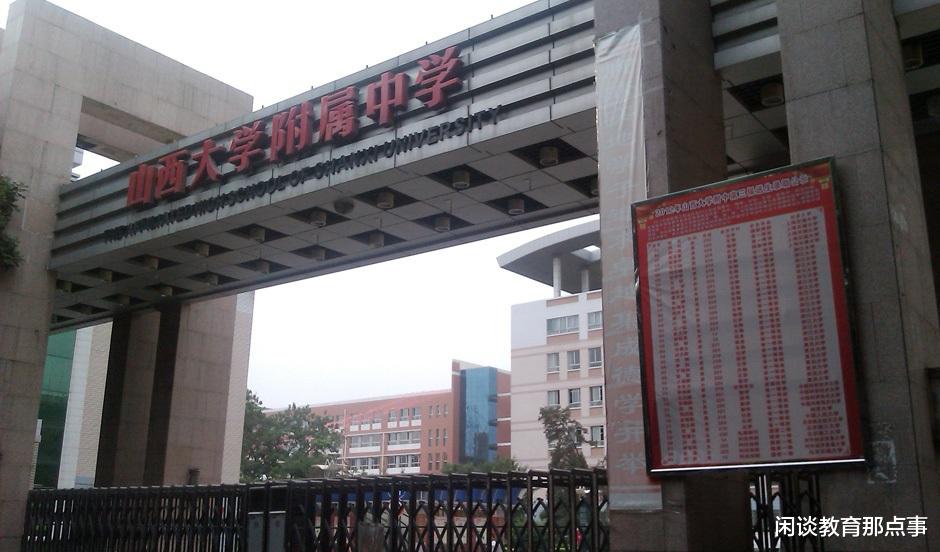十八年前我高考
我是2003年参加高考的。当年最有代表性的集体记忆是:高考第一年安排到6月进行,非典,题超难。
得知高考提前的消息,是通过现在已不多见的放磁带的收录机。当时学校给每个教室都配备一台,便于英语听力学习。这种机器自带收音功能,我们往往见缝插针般关掉英语听力,打开收音机,高考提前的新闻就是这么传遍教室的。
“非典”形势严峻的那段时间,校园实行严格的全封闭,高一、高二学生全部放假回家,只留下高三学生,家住县城的也全部住校。
每天早、中、晚均有专人来测体温并对教室消毒。班里有一个女生,有次体温测出38℃多,按规定要带她到设置在校园内的隔离房。听到这个消息,教室里顿时吵了起来。有火上浇油者说,应该把全班都带走隔离,有追根穷源者,欲搞清楚到底要把她带往何处。经过校医、校领导各种解释,我们才同意放人,但教室里充斥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和“何日君再来”的悲怆、惜别的情绪。没想到第二天,她就回到了教室。她就是上火引起的热感冒,吃点药、多喝水、发发汗,一点事没有。
临近高考的那段日子,师生关系最融洽了。老师们一改之前对我们的高压态势,变得婆婆妈妈了。我们也不会为了防止老师偷袭,在楼道口布置暗哨了。每天的练兵试卷依然如早春飞舞的杨絮和柳絮。有的试题发下来,老师就开始讲,哪些是我们压根就不会的、肯定要出错的,他们早已了然于心。省掉了测试的环节,节约的是时间,敞开的是心灵。我们到老师家蹭吃蹭喝,看会电视,杀盘象棋,权当调节。我们班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称呼男老师为叔,女老师为婶,前面缀以姓氏,指向无误,就是不敢当面这么叫。临近高考似乎也没这些顾忌了,王叔牛婶,我们叫得顺口,他们应得自然。
距离高考还有三天,我们得离开校园了。最后一节课,当然铃声已毫无意义,班主任从手提袋里先掏出已洗好的毕业照,再拿出我们的准考证,依着学号挨个叫,我们一一上前领取。之后,班主任和各科老师又强调了要放平心态、沉着应战,要先易后难、注意涂卡等等,最后都是深深的祝福。我们则报以热烈掌声和尽情呼喊。同学之间的恩怨情仇、鸡毛蒜皮,在这样的时刻都化作义薄云天、肝胆相照的一腔豪情。也不知道谁带了一架照相机,青葱的岁月,定格的瞬间便成永恒。那时还流行毕业纪念册,平日里写个假条都用词不当的,这会都化身文坛圣手,洋洋洒洒、情真意切、感天动地。
回到家里,父母的眼神充满期待。我知道他们想说的话很多,但都浓缩成简单的一句“看看还需要什么”。高考如果是打仗,作为后勤主管的父母,已经做到了兵马未动,粮草已至前线。
高考都在县城。最后一门英语考完,满县城都成了我们考生的天地,仿佛孙悟空摘掉了紧箍,成魔成佛先不管,畅快地先翻几个跟斗再说。当天晚上,《试题与答案》就到了手里,薄薄的一本册子,面对它的,将是面露喜悦者、骂骂咧咧者、壮志未酬者、悔不当初者。估出的分和往年相比,总体低了不少,特别是数学,能估到90分及格线的都不多,能上百的就算绝世高人了,这也印证了数学考完之后,某考点的几个女生哭得不省人事绝非空穴来风。
估完分,报志愿,出成绩,分批次录取,上大学或者复读或者步入社会。高考之后的每一步都如戏剧一样,有主角,有配角,有冲突,有高潮。回忆高考,怀恋高考,是因为经过高考,我收获了丰厚的知识,明白了付出就会有收获,懂得了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是多么神圣和伟大,感悟到青春岁月如金子般可贵,理解了父母亲对我最深沉的爱。(作者:运城市教育局党办 杨国兴)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