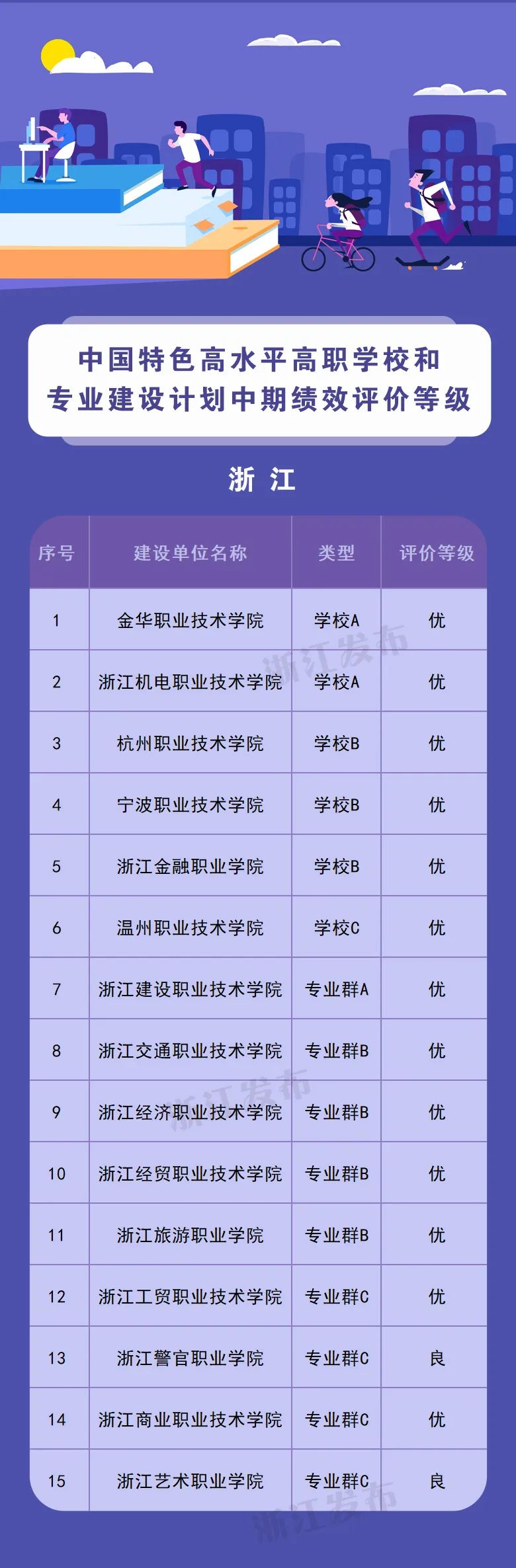陈家明
■本报记者刘如楠
对于从未在国内生活过、如今已经54岁的陈家明来说,近日全职回国,加入浙江大学是个“疯狂”的决定。他把这个选择比作旧时的“盲婚哑嫁”,“我还不了解‘婆家’什么样,就‘嫁’过来了”。
看似冲动的背后,是萦绕已久的心愿——回到祖国,培养人才。近年来国内科研环境的改善让他意识到“好时机来了”,他“要趁着有精力,开辟一番新事业”。
陈家明是细胞死亡和免疫学领域的知名学者。他本科以院校第一名的成绩从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毕业,后任杜克大学教授、免疫系副主任。他在细胞坏死性凋亡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发表论文累计被引用2万多次。
陈家明在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提及自己的科研经历时表示,“失败”是绕不开的话题。他曾连续将一个实验重复了105次,直至取得成功;也曾碍于资历尚浅、害怕出丑而不敢在学术大会上举手提问。一路走来,他希望青年人“永远不要害怕失败,年轻就是冒险的本钱”。
回国好时机来了
《中国科学报》:你在美国学习工作了30多年,已经是杜克大学终身教授和副系主任,为什么选择回国?
陈家明:回国前我在美国发展得很不错,想要做的工作基本完成得差不多了,可以按部就班做到退休。但我一直有个心愿,就是回到祖国培养人才。这对于基本没在国内生活过的我来说,是个比较大的挑战,所以一直没有下定决心。而且我听身边的朋友说,国内很多地方有年龄门槛,不确定是否能找到合适的机会。
近年来,祖国科研大环境迎来巨大变化。一是经济实力快速增长,科技经费投入大幅增加,科研条件堪比世界一流;二是吸引了大批海外归国学者;三是在软环境方面,无论是高校、科研院所对科学家的重视,还是新型研发机构更加灵活的机制,这些都让我觉得好时机来了。我还有时间和精力,为什么不去做一番全新的事业呢?
《中国科学报》:回国对你的家人有什么影响?他们支持你吗?
陈家明:我回国的选择像是旧时的“盲婚哑嫁”,还不了解“婆家”什么样,就“嫁”过来了,这是个疯狂的决定。好在我的夫人非常支持我,她也很希望回到中国生活,我们俩的想法非常契合。
早年,我的父母和岳父岳母出于生活的考虑离开了家乡。他们的思乡之情非常浓,这对我们影响很大。岳父一直希望我们可以回到祖国。至于我们的孩子,已经长大了,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所以我们没有顾虑。
《中国科学报》:你为什么选择浙江大学?
陈家明:在跟学校领导、同事接触过程中,我能感受到大家都有非常强的把教育和科研做好的意愿,非常真诚,这是一个大前提。我们目标一致,其他事情都会比较容易解决。各位老师非常友善,给了我很大支持,我喜欢他们每一位。而且浙江大学医学中心跟浙大第一附属医院挨着,有利于做临床转化方面的研究。
另外,我的父亲去年过世后,母亲一个人从香港回到杭州老家生活,我希望多陪伴她。
一个实验重复105次,永远不害怕失败
《中国科学报》:从本科读生物化学和细胞生物学专业,到后来的分子细胞生物学博士,再到工作后长期从事免疫学、细胞生物学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一直专注于一个领域,你是否有倦怠的时候?
陈家明:没有。我很喜欢我的工作,科研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对我来说都很新鲜。当我解决了一个新问题、改进了一个新技术,或者是培养了一名学生,这些都会给我带来很大的满足感。与此同时,我也能养活自己和家人。天底下哪里找这样的好事?我觉得非常幸运。
《中国科学报》:你在34岁时成为独立PI(学术带头人),从事细胞坏死性凋亡研究,直到41岁时才发现影响其作用的关键因子——受体相互作用蛋白激酶3(RIPK3),从而获得重要突破。这期间经历了什么?
陈家明:2002年我博士毕业后,在马萨诸塞大学从助理教授做起,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阐述一种炎性细胞死亡形式——细胞坏死性凋亡。那时候全世界也没几个人做这方面的课题,我又是无名小辈,所以无论是投稿、申请科研经费,即便数据结果很不错,也总是会被拒绝,得不到认可。
但我还是挺坚定的。我觉得这个工作非常重要,得等到其他人逐渐察觉到这项工作重要性的时候,整个领域才会发展起来,进而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这期间,也会失落、会自我怀疑。我的做法就是,想想家人对我的爱和支持。听起来似乎很老土,但对我是有用的。在我小时候,父母在香港创业非常辛苦,压力非常大。所以每当我遇到困难,就会回想他们当年遇到困难时,如何凭借坚定的意志克服,这会给我很大的动力。
还有我的夫人,她可能不了解研究的具体内容,但陪伴本身就是一种支持。就像这次回国,她愿意陪我一起“疯狂”,让我充满力量。
《中国科学报》:你觉得自己身上有哪些特质,让你在科研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
陈家明:我很爱看体育比赛,科研和体育有共通之处,那就是永远不要害怕失败。打个比方,如果一个体操运动员在平衡木上非常怕摔倒,结果会怎样?如果一位篮球运动员因为害怕投不进,而放弃投球,那会怎样?科学也是如此,如果因为害怕失败、缺少勇气,就停止行动、不去冒险,那永远不会超越自己而获得成功。
我读博士时,有一组实验前后一共做了105次,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每天做重复的实验,每天都失败,很恐怖。我没有动力继续坚持了,非常沮丧。就在那时,电视中正在播放张德培的比赛,我看他身体素质虽然和美国人、欧洲人相差很大,但是他每次都全力以赴跑向那个球,用力打回去。我受到了鼓舞,在第105次实验时,我成功了。
发现影响细胞坏死性凋亡关键因子时,我刚“出道”不久,资金很紧张,但需要花费几万美元去购买材料做筛选,这对我来说是个挺大的事情,所以犹豫了很长时间。最终,我决定买。如果当时没有把“家底”都搬出来,可能不会找到那个关键因子,也不会获得后续的支持了。
当我们每一次站在十字路口的时候,都必须作出选择。选择之后,可能会成功,也可能会失败。但不能因为害怕失败就不往前走,那将永远停留在原地。
迈出挑战权威第一步
《中国科学报》:你提到有个心愿是回国培养人才,在如今这个阶段,培养学生方面与过去会有什么不同?
陈家明:我年轻时,对课题组里的人要求会偏高一些,当走过的路越来越多,现在我会有更多的同理心,更多地理解学生。即便超人也会有跌倒的时候,何况是学生。
回国之后常听到一个词叫“内卷”,其实目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整个世界的步伐都很快,青年人承受的压力都非常大,他们需要更多的鼓励。
《中国科学报》:你通常会怎样鼓励学生?
陈家明:首先是这个世界很大。比如之前去香港交流,我会跟年轻人讲,不要局限在香港这么小的地方,趁年轻多出去闯闯。如今回来,我也是这样劝勉年轻人的——年轻就是冒险的本钱,年轻时多出去闯是非常好的。即便不成功,这些经历也会对你后来的发展大有裨益。
还有就是要有敢于挑战固有思想的勇气。我常常告诉学生,应该聆听和思考长者们的经验之谈,适当地调整工作方向,但是并不一定要按他们说的做。没错,我是在科研上、生活上更有经验一些,但这不代表我说的都是对的。在我看来,要有独立判断、挑战成见的能力,在你的课题上,你就是最权威的人。科学之所以能不断进步,就是因为总有一群人在深入思考、挑战现状、开创未来。如果我的学生是这样的人,我会非常开心,那是我的荣耀。
《中国科学报》:如何迈出挑战自我局限的第一步?你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陈家明:尊师重道、谦虚,是中华文化的优点,这跟西方人的文化很不一样,有时候会导致我们羞于提问。特别是在一些国际会议上,台上讲话的都是著名教授,倍感压力,使我们害怕提问,担心别人觉得这是个很笨的问题,然后出丑。可凡事都要有第一次,我的建议是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和预演,告诉自己这次一定要克服心理障碍,勇于举手提问。慢慢地,这就不是问题了。
上次在学校里听报告时,我跟负责的老师商量,能不能让学生先提问,把提问机会更多地留给学生,而不是让台下的老师先提问,到最后没剩多少时间了。
另外回国之后,我会利用自身的人脉资源,在外开会交流时把青年教师或学生带上。希望有我在身边,他们不会那么紧张。其实我们很多老师的工作都做得非常出色,但如果别人只看到我们在文章中的名字,却认不得其人,就难以在众人中脱颖而出。相反,如果你跟他讲过话、握过手,别人的印象就会比较深刻。我希望帮助我们的老师和学生在国际舞台上更加自信。
《中国科学报》:接下来在建设团队方面,你有什么打算?
陈家明:目前正在陆陆续续招人,我希望今年可以建立一个十几个人的团队。我打算亲自带每一个学生,多花时间跟进组里每个人的工作进度,多和大家交流,能带一个是一个,人太多就会顾不过来。我希望招“徒弟”,而不是“徒孙”。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