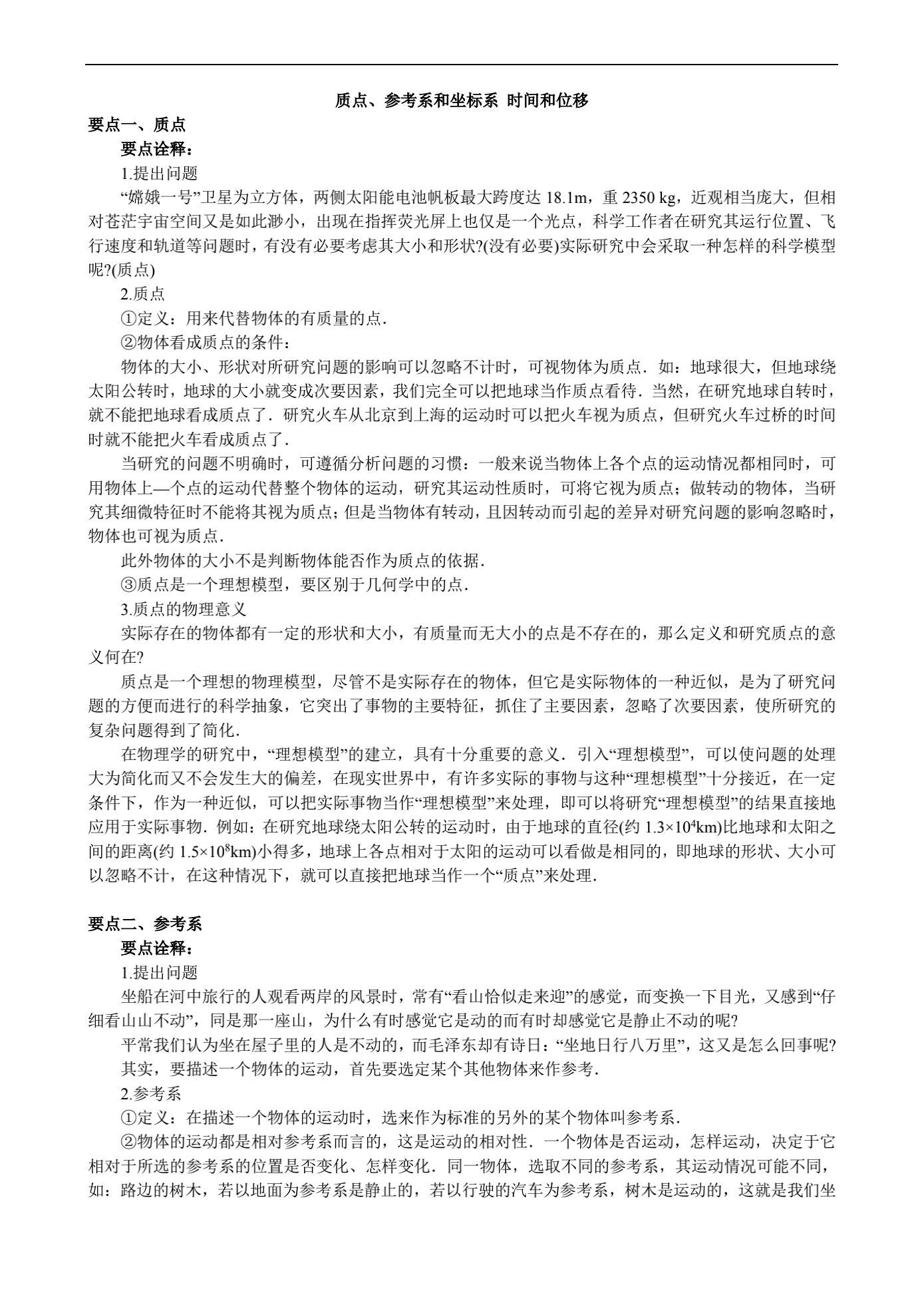零补贴、高强度工作、超长待机,这是综艺节目实习生的常态。整个节目录制现场,像一台庞大机器在运转。在片场奔走的实习生们则是随处可见的螺丝钉,可以被按进任何需要人手的角落。
文|金融八卦女作者:陈尧
1.
/“优中择优”/
节目组入校那天,特地选用了一间面积更大的千人阶梯会议厅。
即使如此,来听宣讲的学生们还是挤满了大厅。
郭涛晚到,被人群挤到座位席后的空隙,身边有人站着,有人蹲着,就这么听完了两个小时的宣讲会。
讲台那侧,是学生们都熟知的团队。近年来,好几部现象级的综艺,都出自这家制作公司之手。公司开放实习生,被选中的学生,将会加入一档热门选秀节目的制作。更重要的是,这就像一张通往娱乐圈的门票,进入节目中火热而愉悦的现场。
一直渴望进入影视圈的郭涛投了简历。和郭涛一样,从千人大会中突围,进入面试环节,只有一百来个学生。第二轮筛选过后,这个数字,将陡降至一到两位。
郭涛是这场面试中为数不多的幸运儿。节目组面向全国几所一本高校招聘实习生,但平均录取率仅仅有0.8%,甚至比某些大厂招聘正职更加严苛。
入组之后,郭涛才知道,团队里有不少北大清华的学生,其余的也都来自国内知名的985/211高校。实习生要么是大型社团社长或是学生主席,要么有类似的节目制作经验。
一起工作时,郭涛悄悄观察过他们,虽然实习生都在幕后工作,但长得好看,也是一项潜在要求。
“优中择优。”郭涛形容道。正是这个高调的开场,给后来的他带来巨大落差。
胡倩是另一档女性综艺的实习导演。她来自一所北方的双一流高校,和许多通过面试的人一样,胡倩将自己的经历总结出来,发在网上。这类“经验贴”,常常引来不少学生围观,大呼“优秀”。
▲图源网络【实习生们在网上分享面试与实习经历】
在网上,她通常只分享了实习的一个侧面。
胡倩常戴着一顶鸭舌帽在节目现场奔走,一只手抓着对讲机,一只手拿着写着艺人出场顺序的文件。有时坐在按键错综复杂的电脑灯控制台调光器前,盯着台上的舞美效果。
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一份令无数传媒学生向往的工作。另一位刚刚通过面试的网友激动写下:“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至于更现实的那一部分,更多人选择缄口不言。
2.
/“平等”交换 /
在知名综艺节目实习,就像半条腿踩进了娱乐圈。“想红”、“成为焦点”、“得到名利”,身边许多这样的声音,开始频繁集中出现在郭涛的世界里。
哪怕只是机会接近喜欢的明星偶像,也足以让很多年轻人为此变得狂热。
给鹿晗庆生时,郭涛抓住空子,对他说“生日快乐”。
那位平日里无法接触到的顶流明星就站在他眼前,朝他鞠躬,说了句谢谢。郭涛恍然想起,青春期时,那些为EXO组合疯狂的日子。
节目排练,黄子韬会在现场与工作人员做游戏;选秀节目里贴心的女艺人,会给包括郭涛在内的工作人员倒一杯水。
郭涛随手拍摄一条明星离开片场的视频,在微博上阅读量超过百万。第一次从艺人身上瓜分到关注,他觉得自己像一个热气球,升腾、膨胀、爆炸。实习结束,他再变成一堆碎屑,回到陆地。
成为综艺节目编导,也是郭涛一直以来的目标。他爱看韩国综艺,希望能在国内制作一档有自己名字的节目。
而实习带来的人脉,才是正式进入这个圈子的钥匙。“综艺编剧或者导演的招聘公告,为什么从不招正职,只有实习生?这中间的人才的缺口,只有通过内推。在一个项目实习,彼此认识,大家一起抱团,就会慢慢形成编剧的小圈子。”
工作机会,往往就藏在人脉网里。综艺编剧们处于半捆绑的状态,找到一个人,就能带着其他人一起“打包销售”,签订合约。
吴倩则想借助这份实习作为跳板,方便毕业之后,进入大厂视频部门工作。她出身汉语言文学专业,却更喜欢摄影与剪辑。大学四年,她把大多数精力都花在上面,经营着一个拥有两千多名粉丝的视频账号。跨专业就业本身就有难度,要想进入大厂,更需要拿得出手的履历。
她研究过大厂人的履历,发现大多数都有与岗位匹配的大平台实习经验。在知名综艺节目拿下实习项目,无疑是吴倩专业能力的最好证明。
▲受访者供图【吴倩在工作现场】
3.
/ 当理想照进现实 /
在节目组待久了,胡倩发现,身边隔三差五就会有实习生离开。
上班时间是下午两点,看似轻松,实际上只是为了应对加班的需要。实习第一天,胡倩就和其他同学在片场工作到凌晨两点。到了第三天,有实习生感到心跳异常,请假到医院做了检查。
胡倩将这份工作形容为“227”,下午两点上班,凌晨两点下班,周末无休。相比之下,大厂的“996”也显得不太可怕。
在片场的大多数时间,胡倩都只是坐在电脑前拉片。一集两小时的综艺,拍摄全程的素材就有七八个小时,甚至更多。她的工作,就是将这些素材逐格播放。平时看综艺调倍速,现在却像抽丝剥茧,抽取每个“有梗”的细节,再按照时间点分隔好,放入不同的文件夹。
节目彩排现场,胡倩看到身边的实习生同事神情呆板,每张脸都写满“累”字。演播室里的艺人们正聊得兴起,有人讲了个段子。这通常会被剪进节目里,配上几个嘉宾大笑的镜头。但胡倩不觉得好笑,她只希望艺人们抓紧进度,好让大家早点下班。
胡倩曾有过一天的假期。
实习生们接到通知,不必到片场工作,胡倩和几个熟悉的实习同事一起约好到市中心玩。走到一半,微信突然响起,有一个广告文案需要临时修改。胡倩在地铁上找了个位置坐下加班。修改意见更新,她不得不一边逛街,一边举着手机写稿。一整天下来,吴倩的精神时刻紧绷着,时刻关注着微信,又担心突然弹出什么消息。
郭涛最害怕的环节,是节目的公演。
早上十点开始,实习生们跟着工作人员到现场录制,一直到次日凌晨四五点,录制结束后,郭涛还得继续负责艺人们的后续采访。最累的一次,郭涛连续工作了二十六个小时,没有任何休息的时间。
工作结束,郭涛像是进入“宕机”状态,意识尚且清醒,但身体已经无法支撑他的任何反应,他连一个表情也做不出来。上车之后,他精神恍惚,很快昏睡过去,人的电量用尽,“就像死机了一样”。
即使如此,吴倩与郭涛所在的项目,已经是业内少见的优质机会。在这里,至少还能拿到补贴,满足房租的支出。更重要的是,只要熬得住,实习生们还能获得转正的机会。而这些,都是普通的综艺实习岗所不具备的。
来自安徽的祥子在大二暑假就进了节目组。这份实习机会,是靠他在各大网站上投递简历得来的。综艺实习岗位极少开放校招,但这同时意味着,实习环境可能更不规范。
报道第一天,祥子与另外两个实习生坐在一起开会,他没头没脑问了句:“老师,我们什么时候下班?”
老师瞥了他一眼,露出惊讶的神情:“你还想着下班?”
当晚凌晨两点,祥子才真正明白老师的意思。工作人员们仍守在会议室里,为没定下来的选题发愁。祥子坐在一旁,一边贡献一些不痛不痒的点子,一边努力撑住即将合上的眼皮。
祥子在工作场地附近租了一间月租1100元的小次卧,方便随时待命。三个月的实习期,祥子只休息了两天。实习生没有薪资,祥子的老师看不过去,私下给了他一点补贴,但远远填不上房租的费用。
第二次在节目组实习,工作刚好赶上春节假期。祥子被要求留下来工作。几个一起实习的朋友中途辞了职,只有他咬牙坚持下来。那是他第一个在外度过的春节。在大年夜,为了照顾一个吃素的朋友,几个实习生在一起聚餐打火锅,却只能吃涮菜叶。
父母觉得祥子疯了,他们不理解,明明随便找一家餐馆当服务员,都要比当实习生强。
零补贴、高强度工作、超长待机,这是综艺节目实习生的常态。
祥子曾碰到过另一个实习工作机会,那是一个地方台的节目组,不仅没有实习补贴,还要缴纳500元的管理费与375元的保险费。他放弃了那个岗位,但也明白,他不去,很快也会有其他人填补上来。
4.
/ 身在围城 /
一开始,没人会将来之不易的实习机会与“剥削”两个字联系在一起。
郭涛与实习生们各自被分配给不同的导师,这些来自国内一流院校的学子们陆续发现,他们的上司学历水平都很低。哪怕是清华北大的学生,也只能跟着从大专毕业的老师学习。实习生们私下开玩笑,把实习项目形容为公司的“遮羞布”——这里的人学历太低,平台一大,脸上挂不住,才疯狂招聘高学历学生,拉高自己的平均值。
高学历没法兑现任何红利。郭涛有时凌晨五点就得起床,剪节目艺人的大头照,或是搬运重物。陪他一起干活的,是位来自中山大学的研究生。论资历,他是参加过两个项目的老实习生,但跟刚来的新人们一样,做最底层的工作。郭涛暗暗佩服他,这是一个合格实习生的自我修炼。
接过节目组发下来的劳保手套,郭涛调侃,自己真是“来搬砖的”。
有一次,一次节目特辑中有做饭环节,嘉宾们留下一两百个脏碗盘。正职员工早早离开,剩下的,由郭涛和那位研究生负责清洗。盘子浸泡在油水里,两人只能蹲着,强忍着恶心洗完。凌晨三四点,洗碗水全都变成黄色,实习生们打包好餐具,再搬运到卡车里。
用知名平台为履历做背书,这几乎是所有实习生的共识。传媒行业尤其重视实践经历。从表面上来看,实习生们获得经验与背书,用人方获得廉价劳动力,这更像是一笔你情我愿的市场交易。
综艺节目的实习期大多只有三个月,只要把这段时间熬过去,就能拿到实习证明。
在祥子的第二段实习中,郭涛做过的杂活,也几乎是他的全部工作内容。
整个节目录制现场,像一台庞大机器在运转。在片场奔走的实习生们则是随处可见的螺丝钉,可以被按进任何需要人手的角落。
一位工作人员让祥子整理资料,没过多久,又有人让他帮忙整理录音。另一个老师远远喊着他的名字,让他帮忙做场记。
场记,就是记录现场发生的细节,方便给后期剪辑的工作人员找出节目的重点。
负责场记的是祥子和另一个实习生。按照指导老师的要求,艺人说的每句话,都要一字不差地记录下来。祥子尝试照做,可打字的速度远跟不上艺人的语速。
他请求用语音软件录音,先用机器翻译成文字,再人工校对。对方却一口回绝,给出不足以成为解释的解释:“没有为什么,我们之前当实习生的时候都是这样做的。”
失衡的感觉开始浮现。有时是因为意义的迷失,有时只需身边人的一个冷眼。
每次节目的收尾工作,都让疲惫的人们避之不及。它们自然而然落到实习生身上。打扫垃圾、复原现场,祥子搬着冰箱一类的道具进进出出,一旁的工作人员连脚都不肯抬一抬。
郭涛很快意识到自己身处“围城”。原本那场看似公平的等价交换,在制作公司强大的话语权下,渐渐向另一方倾倒。
加班、熬夜、低薪,这些并非围城中人的第一关卡。对工作意义发出追问,却没有任何回响,这是最终导致实习生们对原本“梦想”的叛离。
5.
/ 叛离 /
有些日子还是值得怀念的。祥子第一次加入一支综艺的初创团队,人数不多,给足了实习生们发挥的空间。
祥子负责设置户外真人秀的嘉宾路线。为了踩点,他跑到云南待了六天,白天穿着防护衣,在悬崖峭壁下看蜂农割蜜,晚上回到休息点,还要搬出电脑,赶踩点报告。
这个节目,祥子跟着团队筹划了两个多月。他幻想着众人推敲出来的点子一一落地,节目结束时,他会在字幕里看见他的名字。
然而,因为小团队抗风险能力弱,再加上疫情对影视行业的重创,实习结束前,祥子目睹了整个项目的流产。外部聘请来的工作人员被一个个撤走,祥子隐隐感到不安。老师找到他时,他手里还有没来及上报的选题。
当项目被宣布无法推进时,所有人都陷入沉默,三个月的付出全都作废,一股失落感在他们之间蔓延,一个实习生当场大哭。
早在面试阶段,吴倩就能感受到公司对新创意的欲求。无论是面试环节设置的问题,还是七天的训练营,节目制作人有意激发这些年轻生命脑子里的新鲜想法。那是吴倩最快乐的日子,这个充斥着重复、抄袭、山寨的行业,需要外部灵感的冲击。
但那时的吴倩还不知道,随着资本的入局,综艺节目的竞争却变得无序而残酷。深圳本地影视制作机构创始人罗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
“资本主导游戏规则时,刨去节目的传播影响力,一个综艺项目的成功与否,主要看项目能否在预算范围内顺利完成制作。
比如说,一档制作精良、口碑很好的节目,如果制作成本超出预算,那么就算做得再好,资本方也不会喜欢。
假如节目原本的情节与人物策划都很不错,但实现起来如果超出预算,那只能改情节、改场景,将预算降到合理范围内。”
郭涛认识一位业内知名工作室的导演。把每个节目都视为成就感来源的他,最近没再产出有水花的节目。“现在已经无所谓了,做节目就像做任务一样。”导演告诉郭涛。郭涛看见,这个人身上的影视热情,在一点点消减。
当情怀的浪潮褪去,实习生们才看见沙滩上搁浅的乱石。
在祥子实习的最后一天,老师们客套地告诉他:“下个暑假还来,我们可以在这边等你。”祥子表面上“好的好的”地应允,心里巴不得马上离开。回到学校,他很快又看见公司在另一个网站上的无薪资实习招聘,他一阵反感,扭头告诉朋友:“这不就是白嫖吗?”
在第二个月时,吴倩提前终止了实习。以往她喜欢拿综艺视频下饭,结束工作的那几天,她看见综艺,脑子里不自觉思考起节目的设置和结构,一种处于紧绷状态的感觉,促使她立马划开视频。
离开时,她大哭了一场,大学四年,为了所谓的梦想努力着,怎么刚刚进来,就要放弃呢?
理智让她最终走向高强度工作的对立面——考公。吴倩算过,即使是在老家泉州当公务员,拿到的工资,也跟在组里转正之后一样多。但两者的工作量,却天差地别。一起实习的朋友感到意外,这么优秀的女孩,实在有些可惜。
只有吴倩明白,自己无法再承担这样的工作强度:“我们容易把自己想象得太厉害了,其实也不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