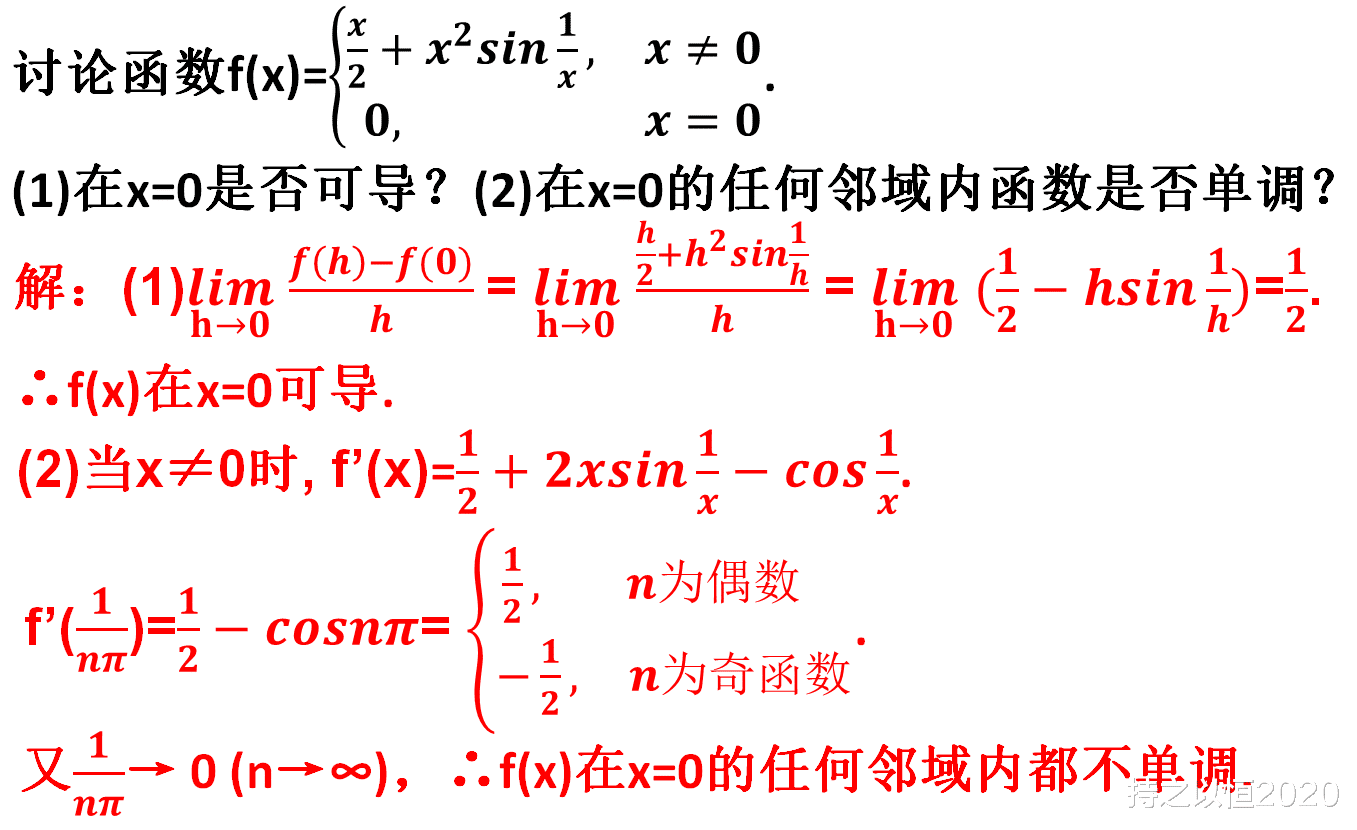北大研究生小伊去年6月毕业,工作270天,她拒绝过一次大厂offer,裸辞过一份高薪工作。
小伊研究生的专业是艺术管理,听起来艺术味十足,但她在毕业后不久就意识到,艺术不能当饭吃,饭不能“卷”着吃,在采访的过程中,她不断强调“稳定”,即便有北大作为学历加持,也并不能带给她多少安全感。
毕业后这14个月,她从一开始下决心找能挣钱的工作,设想自己看在钱的份上可以忍受工作的种种,到现在彻底放弃大厂高薪的offer,只求快点“上岸”,准时下班;从喜欢音乐做乐队主唱,到不敢将其作为事业,担心退休后没有养老金、医保……这种看似更现实、合理的转变背后,她经历了什么?考公为什么越来越成为一种集体选择?
倒3趟地铁,途经23站,耗时近2个小时后,小伊到达西二旗某知名大厂面试海外运营的岗位。
面试开始前,HR告知,这将是一场由3位面试官和十余位候选人组成的群面,时间从中午12点至晚上8点。这次群面后,只录取1人,不再有二面,属于“一场定输赢”。
HR还特意强调,能进入这场群面的同学,已经是从上千名校简历中被精心筛选出来的“优胜者”。但小伊有些恍惚,这哪里是面试场,更像斗兽场,自己和其他人不过是正在被观摩的角斗士。
比拼的第一回合的就是学校和学历。名校扎堆的应届生中,即便自己是北大毕业生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
小伊尽可能在小组讨论中展现自己的逻辑、思辨、组织领导力,但依旧很难出众。她在校期间,除了帮导师做项目没有参加过任何校外实习,而其他候选人手握不止一段互联网实习经历,张嘴就可以说出一连串大厂“黑话”,对于岗位的理解更是直接附上参与实操过的案例。
更“卷”的是,当面试官提问:“你们干过最自豪的事是什么?”收到的答案包括:在海外为公益组织募捐10万元、在印尼拯救大象……但小伊现在已经记不得自己当时的答案是什么。
来自同龄人的压力扑面而来,但小伊不能认输,在接到这次面试邀约前,她海投过四五十份简历,运营、市场、游戏,和自己专业毫无关系的也投。
她还想起老师口中找到“满意”工作的学姐曾说,自己虽在剧院做专业相关的工作,但疫情之下,剧场几乎没有演出项目,收入的全部就是底薪1500元,甚至不足以支撑每月2000元的房租。
小伊劝她,空闲时间不妨接点私活挣零花钱,没想到,学姐立刻反问:你有这样的活儿吗?可以介绍给我吗?
这次群面后,她收到的反馈是:你很好,但这个岗位更倾向招一个男生。HR给小伊推了另一个海外音乐版权相关的offer,本着想找能“挣钱”的工作,小伊接受了这个机会。但仅上岗工作2周后,她选择结束实习,放弃offer。
小伊参加大厂的新人培训
小伊当时所在的部门成立不到一个月,leader也是刚从另一个大厂跳槽而来,她被安排负责商务版权的事宜,每天要做汇报、PPT、查资料和处理一些法务工作。
“这个组除了我,其他同事之前全在律所上班,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在这,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这种困惑伴随着大厂特有的流水线风格让小伊越发不适。她讨厌那些精美的下午茶、餐食、和园区里满足一切生活场景的商店。
“总之有种,你可以一直待在这里,一直工作的感觉。可我不需要这些‘便捷’,我要准时下班。”
小伊在大厂的第一周,同事们每天要耗到晚上10点才有下班的迹象。更让小伊不能接受的是大厂时刻在变的业务线。她开始担心,自己的部门半年之后还在不在,或许下一批“被毕业”的就是自己。强烈的不安全感让小伊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拒绝了这份offer。
之后,她还收到过另外两家大厂的offer,面试分为3~4轮,她刻意让自己“表演”外向,自我介绍的时候还会讲个小笑话。她觉得,这是大厂更喜欢的候选人特质。但面试官仍是匆匆上线,匆匆下线。小伊甚至感觉“卑微”,“明显感觉面试官不care我,因为应聘的人太多了,他要赶紧面下一个。”
那之后,大厂给小伊留下的印象是:高薪、流水线、无效卷、不稳定。虽然后三项让她决定不再考虑任何大厂机会,但对于挣钱,小伊仍抱有期待。她选择入职了一家商业地产公司,听朋友说,这家公司做项目很厉害,待几年再跳槽,赚的不会少。
获得这份地产公司的管培生offer也并不容易,4次面试,上千人选10人,和小伊一起竞聘的还有哈佛毕业生。
比起互联网大厂的流水线面试或群聊,小伊觉得,这家地产公司的面试让她感受到了尊重,一个人一个小屋单独聊,面试官态度温和,平等。
小伊很快适应了新工作,公司口碑不错,待遇不错,离家也近。但没过多久,就迎来了强制轮岗。起初,公司承诺轮岗会根据每个人的适合方向做安排,但实际上小伊被调到离家60公里外的项目中,做并不擅长的招商。
她向领导反馈,这和自己的职业规划不符,但得到的回应是:公司需要你去哪,你就要去哪,嫌远可以在附近租房。
与小伊同期入职的小伙伴走了1/3。小伊选择坚守,她开启了007工作模式。每天她都要见客户、想办法出租商铺,一个人维护60多位店长,不能拒接、漏接这些人的电话。
“他们随时会找我,有时是夜里12点,商家清货,突然没电了打给我;有时是凌晨2点商铺装修搞不定打给我……我已经习惯了,和朋友出去也得时刻盯着手机,不敢放松。”
小伊一边照顾生病的姥爷一边加班
有一次,小伊帮一家奶茶店选店铺,经领导审核通过后,她把备选商铺发给客户,两人约好见面详谈,可一见面小伊却被对方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通。
“你干招商肯定不超过一个月吧?怎么会推给我这个位置?还管培生?你知不知道我是谁,我是我们公司副总裁,你还能加到我的微信?我就不该加你,祝你未来发展的好……”
对方这一通输出后,小伊懵住了。商铺的位置是报给领导审核过的,问题应该不大,她不知道客户哪儿来的火,只在心里后悔当时吵架没发挥好。
在同事眼中,小伊乐于社交,放得开,但她说自己并不是这样的人,所以干得很累。同样,她也不是那种所谓“整顿”职场的年轻人。
曾经,部门有位主管要求所有人停休,连续上班,但主管自己周末照常休息不来上班,且布置的工作也都形式大于内容,组里另一个女生不满这种管理方式向HR投诉,但小伊只是在心里想,如果换做是她,可能不会选择这么激烈的方式。
为了适应工作,小伊也尝试过跟风“卷”。有次,周六晚11点,她被部门大领导邀请进入线上会议室,彩排第二天要讲的PPT。排到小伊讲时,已经凌晨1点,大领导批评她做的内容“没有高度”,让她连夜修改。
小伊想起美国学者大卫·格雷伯曾提及,我们在工作中不断被要求做或修改PPT,是管理者彰显自己地位和权利的体现。而公司里没完没了的会议给报告和演讲提供了舞台 ,使之成为某种至高仪式。但这些PPT的命运大都类似于歌舞伎舞台上道具和服饰,没人会真的仔细看。
对于这些,小伊并非完全不能接受,“非逼着我干也能干,就是膈应。”
最膈应的,是“朋友圈自由”的让渡。那段时间,小伊不敢在朋友圈发和工作无关的内容,因为大家都在整齐划一地发公司广告,领导会检查。开会时,有同事发言说,我们不能把公司当家,因为在家里你想干嘛就干嘛,但是工作的话,不能想还有自己的个人生活。
同事笃定的语气让小伊害怕,她从没想过为了工作抛弃个人生活。但之后的日子,下班时间只要主管不走,大家就都不走,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好像下班、拥有自己的生活、支配原本就属于自己的时间是可耻的。
“公司好像期待员工可以爱上工作,从工作中获得价值感、成就感,以‘忙’为荣,我有很多朋友确实是这样的,但我就是对工作爱不起来,不行吗?”
小伊最终选择裸辞。在离职交接期,她每天一到6点就下班。
离职当天,她还被要求改了最后一个PPT。
辞职之后,小伊在社交平台上写:失去应届生身份让大家更不敢有空窗期,每个人都像拧紧的发条一样往前冲……
焦虑到不行时,她又开始盲投简历,突然意识到这是在重蹈覆辙后,决心暂停下来。回顾两份所谓的“高薪”工作,她发现即便是看在“钱”的份上,也不能忍受工作侵吞生活。
小伊的生活离不开音乐,她知道自己不爱工作,成就和价值感几乎全部来源于音乐创作。她外表甜美乖巧,喜欢穿JK制服,但欣赏的歌手却是如椎名林檎一般个性十足的音乐人。
不上班的这段时间,她和朋友一起组乐队,取名焦螺,希望他们的歌能给每个焦虑如陀螺的人带来一点慰藉。这段时间,他们偶尔到购物中心举办的市集演出,去相亲主题的咖啡厅唱情歌,定期做线上直播,收支也算平衡。
小伊玩乐队
到这里,小伊的故事似乎变成了厌倦职场后,投身热爱,然后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但现实是,她几乎没有想过不上班,相反,这段时间小伊积极准备考公,参加体制内工作的面试。
小伊的父母,就是纯靠音乐为生的自由职业者,在她看来,这样的状态年轻的时候很“爽”,但老了之后呢?养老金、医疗保险这些很现实的问题呢?
虽然对于高薪的执念被前两份工作打消了,但追求稳定成为小伊下一份工作的核心目标。
体制内,在小伊看来就是安稳工作的同义词。
在采访时,小伊主动和我谈起,今年4月北大一位博士考城管的新闻。在那则新闻中,朝阳区公布了208位拟录用公务员名单,其中131人学历为硕士,74人为学士,2人为双学位,3人为博士。毕业院校含清华、北大、中国政法大学、外交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澳门大学等。
小伊有一位学姐,研究生专业是艺术史,毕业后回了老家当公务员。对这个选择,院系里的老师们耿耿于怀,恨铁不成钢地叹息:白培养了。
小伊所在的专业每年只招收6~7人,和一坐就是上百人的阶梯教室不同,小伊们的课堂更是小班私塾,因为人数少,老师们总带着一种传授“孤本技艺”的心态讲课,所以自然希望这个专业的每个同学都能坚持干这行。
小伊刚入学不久的时候,觉得老师对学姐的“责怪”也可以理解。但现在,她也做了同样的选择。上个月,她刚刚和150人一起竞考朝阳某街道的一个宣传岗。
博士考城管,名校生进街道,这种新闻在网络上很容易引发争议。小伊表示自己能理解网友们的评论,但马上补充道:他们不太了解现在就业有多难。网民们不了解,老师们也不了解。
据《清华大学2021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显示,清华大学2021届签三方就业毕业生总数为3669人,其中去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人数合计占比为69.9%,也就是说,近7成清华毕业生选择进入体制内。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提到,前些年,大批211、985高校毕业生不肯进体制,他们要去创业,在咖啡馆里总能听到谈论融资的火热场景,但现在咖啡馆里的话题变成了各级各类单位的考编、考公,申论怎么写,面试怎么过,年轻人似乎变得越来越“不敢”。
可以理解的是,在疫情影响下,大环境中充斥着许多不确定性,人们渴望获得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首先就体现在职业上,工作稳定,个人生活才有想象的可能。
但为什么考公似乎越来越成为获取安全感的“集体选择”?
首先,在Z时代年轻人心中,工作的意义正在减弱。小伊从没把工作当成获取个人成就感、价值感的来源,在她看来,工作只是维持稳定生活的工具,她的期待、希望都和工作没什么关系,相反,她更看重作为音乐的副业。
正在录制歌曲的小伊
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名校毕业生也要做好“面试造火箭,上班拧螺丝”的准备。
而这种落差感,或许可以用大卫·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中的一段话作为答案:
“当你被雇佣时,你感到自己是因为有用才获得这个岗位的,结果却发现事实完全不是如此,你甚至需要假装自己有用,假装这个岗位有用,这种先让你产生自己有用的错觉,然后再被全部否定的经历是对自尊感的摧毁。”
那么,既然小伊已经降低了对工作的期待,为什么还一定要有一份工作呢?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口中的“上岸”指代的都是体制内的工作?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家德认为,这和年轻人可参照和拥有的机会变少有关。小伊的好友也在体制内工作,作为距离她最近的参照,好友确实可以做到准时下班,周末不加班,而其他安稳工作的参照和机会,并没有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小伊的学长学姐们,有人选择了留校,但是属于合同工,没有“编制”,只能苦熬转正机会。
上个月小伊在落选朝阳街道的考试后,又报考了一家事业单位,采用线上考试,40人一场,两个小时,小伊觉得自己考得一般,但仍被40人同时在线作答的场景震惊。
眼下,小伊一边做音乐做乐队,一边准备考公。跟她一起做乐队的小伙伴都是兼职,贝斯手在一家国企工作,键盘手是小伊在商业地产工作时的同事。三个人都是95年生人。
每天,小伊的生活节奏是:早上开始做歌,下午去上声乐课或舞蹈课,晚上做直播。她之前几份工作的积蓄,还能支撑一年左右的无固定收入状态。
2020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小伊创作了一首叫《女孩》的歌,激励远方不能回国的同学,激励在海投简历中怀疑人生的伙伴们:
女孩,你剪短了长发,剪掉的忧愁就送给我吧
女孩,你习惯了笑脸,深藏的眼泪能告诉我吗
女孩,你收起了行囊,不要的杂念就留给我吧
女孩,你去向了远方,遗忘的过往就交给我吧
不需要美丽动人,似水情深,或是火焰般青春
只要懦弱的,胆小的角落里的你啊
也许有一天转过身会发现影子的背面
那里有我微弱坚决的呼唤
我最亲爱的女孩啊,勇敢前行吧
我是迷途风景,也是昨日的你啊
如果你把温柔都交付给了TA
不完美就留给我吧
我最亲爱的女孩啊,不要回头啦
越过坎坷山川,拥抱满怀的晚霞
哪怕路途遥远,有人把你牵挂
最初的愿望,实现了吗
上下滑动,查看《女孩》歌词
那一年,小伊在家待了半年。疫情刚刚缓解,就被严酷的就业环境唤回了现实。从高薪崇拜到回归稳定,她不停地试错,不停付出代价。
小伊的父母是70后,都是自由艺术工作者,从小到大,他们对小伊的态度都是“你高兴就好“,不管是大学选专业,还是选工作,甚至离职,父母都支持。小伊的压力更多来自朋友圈,看到其他人丰富多彩的生活状态,会觉得自己浪费时间。
我问她,如果时间可以倒退回研究生考试,甚至高考,她还会选择现在的专业吗?
“我想我会先研究下这个专业未来的就业方向,待遇,然后找几个目标单位提前问清楚,不会再只想着喜欢不喜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