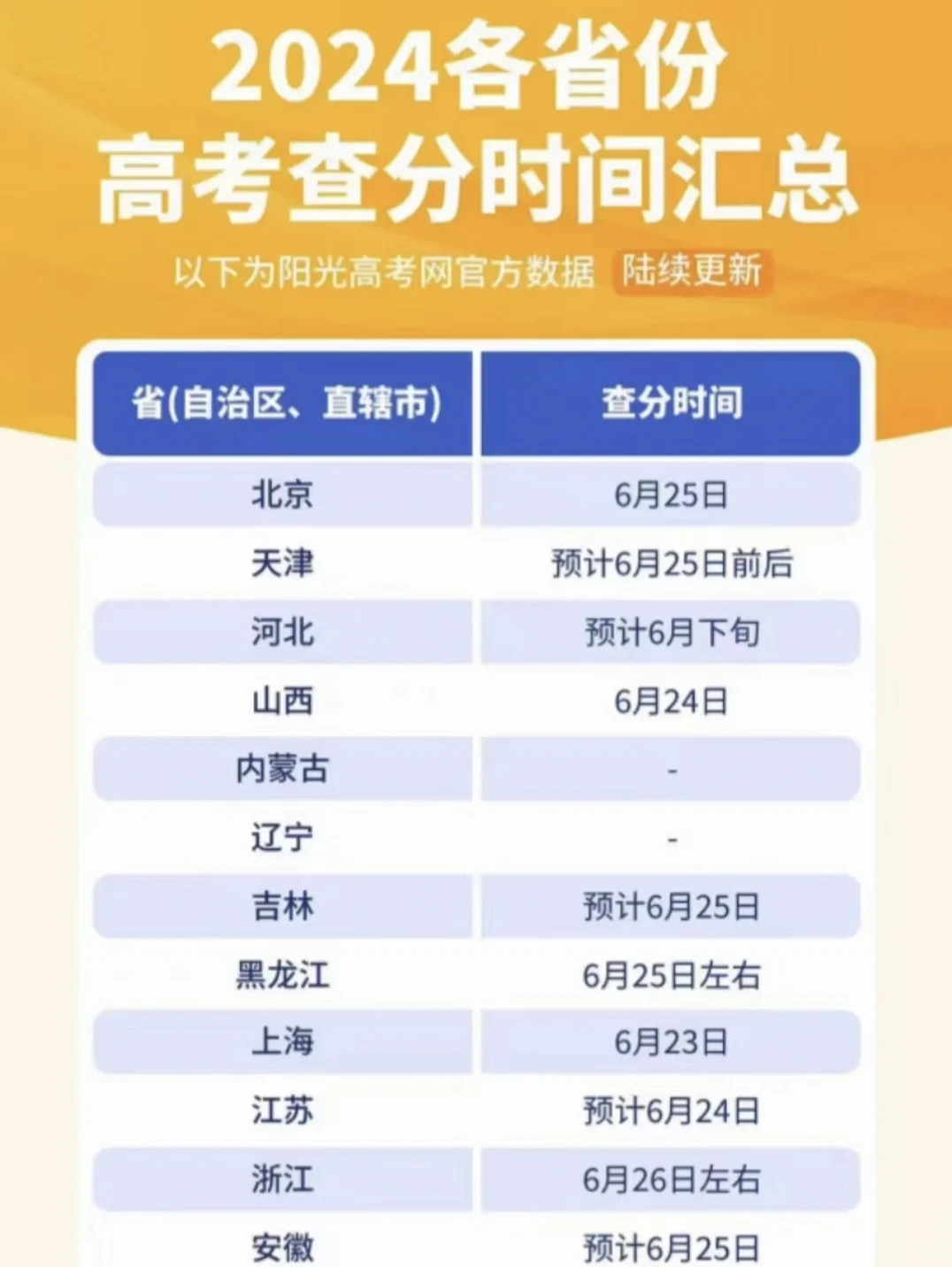黄修志是鲁东大学的一名任教老师。从2018年起,他开始了一场教育实践:让班级每位同学担任一个月的“历史学家”,轮流撰写班志,记录班级大事记。他想带领学生在书写中观察他者,在他人的记录中觉察自己。2024年1月,这部由师生共同书写的《班史:一个大学班级的日常生活》出版。
但这不是我们想关注和书写它的唯一原因。这是一所前身为师范学校的二本院校,位于山东烟台,当地是出名的考公大省。与一般意义上的“二本学生”不同,鲁东大学的学生们很少为自己的出路担忧,相反,他们有明确的目标,“当一个公务员”、“成为一名研究生”。
从现实层面上看,这些都是更为体面的人生选择,但黄修志发现明确的出路背后,隐藏着学生们更大的焦虑。大多数学生找不到自己的兴趣所在,被世俗的标签所框定,只是蒙着眼睛往前走。
无论是学历还是就业,二本学生面临的束缚是一个客观事实,他们的困境是这个时代年轻人面临的最广大的困境。那么身在其中的教师和学生可以主动做点什么?
做班主任的这几年,课堂内外,黄修志带领学生们做过许多尝试。他们举办跨学科讲座,创办石榴花杂志,办读书会,写书评。所有这些活动,并不在教材里,也很难用绩点来衡量。它更多来自校园生活里具体而微小的实践,知识之外,学生们锤炼品格,建立世界与生命更广阔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这场教育实践还有一层丰富的意涵——这所学校,是在为胶东半岛培养未来的中小学老师。这群年轻人,回到家乡,走上教师岗位,像落地的种子,继续传播这些鲜活珍贵的教育经验,改变微小的气候。
“希望可以成为一个公务员”
“大学四年以后,你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2018年秋天,文学院108教室里,班主任黄修志第一次和他的学生——汉语言文学专业1801班42名同学见面,他给学生们发放了一张《初心与理想》的表格,向他们提问。
问卷收回来,有同学回道:“希望可以成为一个公务员”,也有同学答:“成为一个研究生”。
这些答案让黄修志哭笑不得,同时又困惑,为什么学生会这样想。
1801班的学生来自四面八方,又有着相似的成长背景:他们是首批进入大学的00后,全班42位学生,有28位都来自于山东,大多数人生活在镇上,而非农村。大多数父母都在体制内工作,职业是老师或者医生,也正因为此,许多学生一进大学就知道自己要考公、考研。
孙玥璠来自山东威海,高考报志愿时,她填的是英语专业,因一分之差没有被录取,滑到了汉语言文学,但这也无关紧要,“我还是可以成为一名语文老师”。她的家庭里两个阿姨,上一辈的姨姥、姑姥都是老师。从小,她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是:长大后,当一名老师。分不清是自己的愿望还是父母的期待,这个念头扎根在她的心里。
张佳怡报考文学院的想法很简单,逃离数理化。她是理科生,但真正感兴趣的是文科,父母觉得学文没什么前途,高中三年她硬着头皮学完。当得知鲁东大学的文学院也对理科生开放时,她毫不犹豫地填报了,进入学校她发现,和她一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
王月的家乡在云南,她的高中生活是在纯粹的应试中度过的。她埋头做题一点点挤下千军万马,顺利进入昭通市一所中学——全市最好的高中。但高考她考砸了,心里有些不甘心,报志愿的时候她胡乱填了几所学校,被鲁东大学录取。山东离家很远,她记得刚开学,恰好是烟台的雨季,街上的垃圾被风吹得乱飞,她自我安慰,把上大学当成是体验北方不同的生活。
张鑫是班级里仅有的三个男生之一,父母都是青海牧民,高中在离家200多公里的县城求学。他是村里唯二的大学生,另一个是他的弟弟。能考上鲁东大学这样的地方院校,他很满足。
如果说黄灯老师笔下的二本学生聚焦在80后90后的农村,那么新一代00后很不一样。来到这里的学生分两种心态。一部分学生懵懵懂懂,心里没有主意,他们跟着父母的期待走,加入“考研,考公,考编”的大军。还有另外一部分学生则相反,他们对体制很反感,报专业时扭不过父母,失败了,内心陷入迷茫。
鲁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戴宗杰觉察到这一代学生们身上,存在着一种矛盾的心理,既有一种强烈的不服输感,希望通过考研重新证明自己,又感到强烈的自卑,“他们看上去很努力,但不知为何努力”。
黄修志也从学生脸上看到了疲惫,“学生都很青涩、内向,九成的人戴着眼镜”。班会上他让学生列举自己最喜欢的5本书,不少同学的答案平平。“进入大学前学生们备考、刷题,在缝隙之中的刷视频和游戏,占据了他们前几年的全部生活”。
这是黄修志教书的第六年。2013年,他从复旦大学博士毕业,开始在鲁东大学任教。第一次担任广播电视编导班的班主任,他决心引导好学生,在教务办办公期间,每次午休便把同学们叫来聊天,并在每个季度推荐书籍。
但学生普遍对阅读没什么兴趣。一个学生很直接地跟他说,“看这些书对考研没有什么用”。
在山东省,鲁东大学与曲阜师范大学、青岛农业大学、聊城大学并称“四大考研基地”,以超过30%的考研成功率闻名。学生们普遍很忙,需要学的课太多了,大二的时候他们就要决定考研的专业,甚至来不及享受美好的大学时光。
图/第一次班会
曾有台湾地区的学生来交流,看到走廊、楼梯里,都是背题、读书的学生,大受震撼。台湾学生告诉黄修志,在台湾,大家都在玩手机、打游戏。黄修志安慰式地解释,这些都是在考研的学生,在背英语、政治,“不见得真的在读书”。
他提到复旦大学求学时期的读书氛围,课堂没有太多的知识讲授,许多时候老师和学生坐在一起读一部经典,你一言我一语地讲。成为老师后,黄修志想复制读书岁月,把当年读书的氛围带过来。但学生们不回应、不愿听讲。
2017年,他在遗憾中送走第一届学生,他承认“不太成功”,所有人都“尽力了”。
自由的边界
做1801班的班主任时,黄修志刚迈入30岁门槛。此前,他被借调至教育部工作一年。跳脱出学校环境,他进行了更多的观察与思考,重归教师岗位,他要求自己能主动做一些事情。
一次军训结束后,学生赵婉婷找到他,向他提出自己内心长久的困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她说起自己高中时“除了学习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可做”,进入大学后她失去了动力,有些无所适从。
黄修志没想到会面对这样的疑问。之后的几个月里,他挨个找学生谈话,聊天的过程中,类似的问题不断涌现:有学生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学习,大学上课老师不划重点,他发现以前学习的方法失效了;还有的同学苦恼于读书很慢,记不清外国人名,读了前面忘后面。黄修志看到学生们的困惑,为这代年轻人的处境担忧,他觉得自己没办法转过身,不去回应。
第二次班会,黄修志提出了一个贯穿大学四年的计划——写“班史”。“每位同学担任一个月的‘历史学家’,轮流撰写班志,记录班级大事记。”他向学生们说出自己的构想。
他想带领学生一起做一件事,帮助他们在对彼此的观察中进行一种对自我的审视,同时寻找自我,认识自我。
写班志的想法来自于他的经验。苦闷的大学时期,阅读与写作带给他许多力量,“把像死疙瘩一样的郁结一条条写下来,自然便能剖析自我,梳理清楚自己的心”。
黄修志给学生提出要求,文章太平淡或是太艰涩不行,要带着“历史学家的视野”,记录班级发生的事,不能太散,不能写成个人总结。
写班史一开始进行得不顺利,学生们感到困惑,不知道该怎么写。常佳珍交出了第一篇文章,她把开学以来的所有事件密密麻麻地写了两页A4纸。黄修志解释,不是写流水账,写作是一种日常生活的状态。
在这之后,他给学生办了一场讲座——“作为日常生活的写作”。黄修志站在讲台上就是鲜活的教材,他讲自己求学时的经历,也讲青年时代的苦闷。
黄修志与学生们有相似的起点,本科也毕业于一所二本学校。
1987年,他出生于山东东平的乡村。高中时期就读于县城一所普通中学。他在班级名列前茅,却在高考中发挥失常,考入聊城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那是一所二本院校。他想过复读,他的父亲说,“你已经是咱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了”,他放下执念,入了学。
进入大学,黄修志对所学的课没什么兴趣,老师与学生也没有过多的交流。他喜欢读书,一次课后,他追着老师,请老师推荐书目。“我回头想想再告诉你”,老师这样答道,就匆匆离开。他知道老师不会来找他,他来不及要联系方式,老师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没有平台没有资源,黄修志感到苦闷,他找到了和他一样喜欢读书写作、发表观点的同学,他们自办讲坛,大胆评论公共议题,自在谈论天地。人群中他们被视为“异类”。
2007年,黄修志考入武汉大学攻读文学硕士。进入名校,他才体会到普通高校与一流高校的区别。
在武大求学,他遇到了对他影响很大的老师。上《中国古典文献学》和《海外汉学史》的教授于亭,她告诉黄修志读书不要求新,而要读常见的经典,只有下盘足够稳,根基足够正,学问才能做得好。于亭研究海外汉学,向他推荐了很多历史学研究的书,从那时起黄修志的兴趣发生了转移。
图/在租房内读书
当时他有一个颇具浪漫主义气质的信念,觉得人文科学就应该多去游学,到不同的文化区看一看,读个不一样的专业。最终他被复旦大学历史学院录取。
喜欢和做研究是两回事,进入复旦大学后,他从最经典的历史学的论著读起,读史料、读材料。同时也经常跑到哲学系参加读书会,也会旁听物理系的课。
求学路上,黄修志横跨了三个不同的专业,这个过程中,他意识到各个学科的优势都在于用解释框架从特别的视角来解释问题,而不是受限于某个学科。在大学,他获得了一些探索的自由。
十几年后,黄修志慢慢回味出自由探索的意义。
他告诉学生,“进入大学就应该自由的探索,和更多的人相遇,理解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选择,找到自己热爱的东西,投入进去。”
受到黄修志的启发,学生们开始自由创作。常佳珍写下自己刚进入大学时的画面,搭乘“咣当,咣当”的火车;秘若琳写下一路求学的困惑与挣扎,“我对自己有更多的期待,没有想到会被二本学校录取,心里是不能接受的。”;赵婉婷写下与同学的友谊,“我们在晚上聊意识,聊文学和意义,以及永恒”。
学生们开始在班志里有了更多的思考,更多的表达。
一块精神世界的飞地
鲁东大学坐落于山麓与山坡之间,从鲁大佳苑上坡下坡进入教学区,会看到南1宿舍楼一楼的一排宿舍,群山间构成了晨钟暮鼓的日常风景。
旁晚时分,大一新生坐在教室里上晚自习。这天,黄修志直接走进学生的自习教室,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个问句:“对你们来说,语文是什么?”
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方向的师范生,大家面面相觑,语文就是语文,这个话题还用讲吗?黄修志不紧不慢,他请学生拆分来看两个词语,可以有怎样的解读,有人说“语言文学”,有人说“语言文字”。接下来,黄修志把语文分成语言文字,语言文学,语言文化,语言文明,四个层次来讲。
他讲到文字,比如“它”这个字,一切非人类的东西都称之为它,它的本意是什么?有着怎样的历史文化?最后,黄修志说我们认识的语文,跟要探索的人文科学不一样,应该有一种大语文的观念,不是为了做好一个题,而是要广泛地去阅读,认识世界。他希望破除学生们对专业狭义的认识。
黄修志和学生们边讲边聊,当时汉本180班和汉本1802班的学生共用一个自习室,许多学生觉得奇怪,“这个老师怎么突然到晚自习给我们讲课来了?”意外的是,学生们没有走。陈奉泽听完后当晚给黄修志发来微信说,感觉到自己以前的语文白学了,更新了很多以前的误区。
接下来几天,黄修志趁热打铁,他给学生讲“怎样读经典”。这些讲座都是自发的,学生旁听,不算学分,没有任何功利性的好处。
但在他的课堂,来听课的学生很多,黄修志从学生身上看到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对于求知求真的渴望。
一次,学生路棣向黄修志求助,他苦恼于很难摆脱高考作文的写作模式,想要自由地写作却找不到方法。黄修志不是作家,解决不了这方面的困惑,他想到鲁东文学院有一位名叫周燊的老师,是一位作家,也是王安忆老师的学生,他便邀请周燊为学生们上了一次课。
二本院校没有太多的资源,学生们没有平台、经费、师资、人脉,也很少有推免读研、出国交流、斩获高额奖金的机会。“在名校,哪怕班主任不做过多引导,学生也很可能独立成才,可在学生基础不一的二本院校,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建立起共同体,实现自我突围。”黄修志说。
他通过私交来邀请学者做讲座,从周燊老师的讲座开始,跨学科的“石榴花大讲堂”拉开帷幕。不同背景的老师来到班级,讲述自己的研究经历,从文学、历史学,讲到人类学、法学、艾滋病学……
王月去听了一场讲座,讲课的是一位姓周的女老师,20来岁很年轻,她讲述自己的经历,让她心生敬佩。她问老师,怎样才能像她一样多姿多彩。老师告诉她,不要轻易给自己下定义,需要经历之后,才会发现你想要成为哪种人。
以前,王月觉得人和人太相似了,对好生活的定义越来越狭窄——上大学,找工作,稳定下来后家里人就会催结婚生孩子,大家都在做,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但现在,她发现自己的想法再慢慢变化,“心里会有一点摆脱束缚的感觉”。
图/班内同学在主题班会上做演讲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任海涛曾为学生们做了一场线上讲座,以校园欺凌为切入点,分享跨学科学习经验。同样的讲座,任海涛在十几所学校讲过,而在鲁大,他感受到了一种不一样的氛围。有学生问“文学和法律有什么关系”,也有学生问他,“从文学角度怎么研究校园欺凌?”这些问题其他学院的学生都不曾想过,那场讲座开了近三个小时。
我们采访的时候,那段读书的日子已经远去了。在学校作为石榴花读书堂宣传部部长的张佳怡,现在,她是内蒙古一所小学的语文老师。她仍然清晰地记得,当时每周她会认真读完一本书,有时也会和室友讨论,她喜欢古代文学,室友对现当代文学更感兴趣,她们就彼此的分歧向黄修志提问。
在文学的海洋里,张佳怡体会到一种纯粹的快乐,她在班志里动情地写道:“文学教会我的,是做个闭眼的愚者。用我觉得合适、习惯的方式去写去描述,那些捏造的语句的意义在我,理解在我。”
黄修志鼓励学生上台说话,每次班会后都会安排一个小的演讲环节。学生李孟凡提到,一次班级举办博物馆奇妙夜的活动,让大家各自去分享家乡的博物馆。她来自山东东营,当地的博物馆在大型的博物馆面前没什么特别的,但她做了许多准备,当她把看到的能够展现东营文化分享给同学们时,她非常兴奋,变得非常自信。
在胶东半岛这样一所二本学校,师生们建造了一块精神世界的飞地。他们办读书会,共同创办《石榴花》杂志,学生们聊人生,聊国家大事,什么问题都能聊,想写什么也自由去写。
图/2021年11月,石榴花读书堂成立两周年大会
严酷世界
看上去这是一个理想大学生活实验,走出校园,他们仍然要面对残酷的现实。大三下学期,学生们去往山东的各个中小学实习。有的学校地处偏远,他们得以看见真实的各个乡镇中学的状态。
王月被安排到一所乡镇中学,课堂上她发现听课的学生很少,下课后学生会说脏话,骑摩托车在街上飞驰,离她想象的课堂相去甚远,“以前把学生想的太理想化了”,她说。
学生们接触到更多的信息,了解到自己的处境,不免会产生一种落差感和心理波动。
实习的过程中,李孟凡发现自己不适合当老师,“对学生缺乏耐心”。当时她的室友们都在准备考研,氛围之下,她倍感压力。
2020年,教师黄灯的非虚构作品《我的二本学生》记录了对二本学生的真实观察,书中作者提到:“他们的去向,更是在严酷的择业竞争中,有着触目可见的天花板。”
李孟凡提到阅读《我的二本学生》时的感受,脑海中闪现出一个词:选择。“每次放假回家所要面对的两种规劝,一种说:考研吧,现在社会本科生混不开的;另一种说:体制内好,考个编制又稳定又轻松。”人生的选择似乎已经被限定好了,篮子里只放了两个鸡蛋,等待着她去选择。
前置学历依旧是二本学生挥之不去的烙印,就连考研也带着功利化的目的——实现学历上的跨越,成为211,985的学生。
李孟凡意识到现实的残酷,权衡之下,她决定向体制内靠拢。我们记录的当下,1801班的全体学生已经走入社会两年,李孟凡回到家乡,成为了一名公务员。
“二本学子”的学历困境,黄修志有着切身的体会,他清晰地记得两个瞬间。2013年夏天,他博士毕业,参加一所浙江省属高校的招聘,工作人员翻了翻他的简历,还给了他,“本科不是211,三个专业也不一致,你希望不大”。
另一个画面则是,他写下与鲁东大学的就业协议,一位老师看着黄修志填写工作单位名称,不禁问:“鲁东大学?鲁东大学在哪儿?”这让他一时语塞。工作以后,博士导师邹振环曾给他发邮件,告诫他,“现在你应该忘记自己是复旦大学的博士,内心不要经常记着在复旦研究生期间的辉煌”。
学生们毕了业,要谋生活,不得不进入某个系统。张鑫曾想到内地闯一闯,但他是回族,饮食习惯上有诸多的不方便。“打个比方,如果领导有饭局叫你去,去了又不吃任何东西,这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说。最终他也回到了青海的一个县城,在事业单位里抄材料、写汇报。进入体制后,他感到很乏味,“可能哪份工作都是这样。”
临近毕业时,1801班有37人参加了考研,是鲁东大学2018级最多的。学生们拼尽全力,成功考研的只有9人,此后的两年间,又有4位同学三战考研上岸。
孙玥璠三战考入宁夏师范大学研究生,今年9月,她将在此入学。刚毕业时她曾在威海一所小学当老师,属于编外人员。她马上看到了头顶的“天花板”。“如果只是本科学历,今后我要教更高的年级,连报考都没有资格。”她被自己的学历所限制,反复思量后,她裸辞考研。
对于同样三战考研的王飞来说,考研是一条更为艰难的路。2022年她第一次考研,由于报考人数众多,所选专业录取线比往年暴涨了十几分,她差两分没有达到调剂标准。第二年到面试环节,她没有发挥好,又一次被刷了下来。第三次她才顺利凭着调剂进入了一所大学就读研究生。
采访时几乎每个人都提到了就业的严峻,几年前对于年轻人来说,初入社会还有试错的成本和机会,现在这个窗口期越来越短。
年轻人要达到自己的理想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代价。
秘若琳是个腼腆内向的女孩,读中学时她喜欢阅读,爱好文学,但她最终还是听从了父母的建议选择了理科。进入鲁东大学后,她在园艺专业迷失,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直到大一下学期,她获得转专业的资格,进入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二她选修了社会语言学,对社会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并萌发了跨专业考研的想法。在被鼓励说出自己的想法前,秘若琳蒙着眼睛被父母的期待推着走。几次百转千回,她找到了自己的热爱,如今正在南开大学读社工与社会政策专业。
图/2021年1月,雪中的鲁东大学
大学的教育,可以多大程度上改变学生们的未来?
或许并不能改变多少。作为班主任黄修志很清楚,1801班的学生90%会走向教师岗位,真正走学术道路的不会超过3个人。即便学生们考研上岸,职业道路也不会有太大的转变。
黄修志了解现实的坚硬,难以用课堂上那方理想的小天地去碰撞。
2021年6月,作为指导老师,黄修志来到临沂调研了当地6个县的乡镇中学。在这里,他遇见了曾经在鲁大文学院的毕业学生徐蔓。对方对他说,班级五十多个学生只有两个学生在认真学习,黄修志感到难以置信。
后来在跟教师访谈中他发现,为了孩子能够上好的初中,经济条件不错的家庭早就到县城到市区去买房了。留在乡镇初中的孩子多是父母常年在外打工,由爷爷奶奶隔代教养长大。
黄修志受到震动,“现在大学里有多少是特困生呢?他们没有我们聪明吗,还是阶层固化让更有权贵的人拥有了更好的教育资源?”他来自乡村,作为村子里少数的大学生,是整个村子的骄傲。但现在环境已经不同了。
图/2021年6月,黄修志看望各县中小学实习的学生们
落地的种子
这几年,黄修志去往各个中小学,给老师们做一个写作方面的培训。他观察到不少中小学语文老师不读书,也没有写作的热情,他们是没有时间么?黄修志为这个现象感到担忧,他问华东师范大学的王意如老师,“为什么语文老师不爱读书?”
他们说起语文教育,谈到教师的“底气”。它来自于两个层面,一是在读书量上压倒学生,成为学生读书的榜样;二是读书所得随时转化为“教学机智”,学生从低阶到高阶的知识迁移需要教师通过广泛阅读来在课堂上架桥铺路。读写所得就像火箭燃料,燃料越充足,飞得就越高。
做老师的这几年,黄修志察觉到自己有一个转变——以前他认为培养一个优秀的研究生只需要做好本职工作就行了。但现在他想,与其这样,还不如培养更多优秀的语文老师。
我们关注鲁东大学校园里的教学实践,也正因为它的特殊性——这所学校,是在为胶东半岛培养未来的中小学老师。据《鲁东大学2022-2023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烟台市基础教育教师中,鲁大毕业生占53.6%。大学所形成的书写与阅读的习惯,包括看待世界的多重视角,会影响他们,在更广阔的土地上得以绵延。
张佳怡回到内蒙古老家在一所小学做语文老师。比起应对考试,她更在于学生们真正能学到什么。最近她们学习神话故事,以往的教学框架中,老师只需要把故事讲清楚,故事是怎么写的,体现了什么中心思想,做题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张佳怡不想这样,她会尽力扩展课程内容,她给学生讲盘古开天地,讲神话的体系,讲外国的神话是神直接创造了世界,中国的神需要经过许多努力。这些对考试没有什么用,但她相信一些观念会在孩子们的脑海中慢慢形成。
图/已遍布全校的《石榴花》杂志架
孙玥璠提到做老师时,有一次去家访,家长抱怨孩子看漫画书,担心孩子耽误学业,了解过后她发现学生看的是一本关于历史的漫画,她对家长说阅读是一种好习惯,不用局限于他们读什么书,反复和家长强调鼓励孩子阅读的意义。
同样成为老师的王月也在进行着教育实践。她在云南一所公立学校教高中语文,初入工作岗位,她也想像黄修志一样让学生们去记录高中三年的生活,但这个阶段学生们面对巨大的考学压力,没有空暇时间,她就利用课前5分钟,鼓励学生上台分享自己最近读过的书。
这场阅读分享没有延续下去。学生们羞于表达,有想法的人很少,“他们熟知抖音上的热梗,却对苏轼、陶渊明的故事知之甚少”。高中阶段的教学任务又紧又重,王月觉得在现行教育体制下,限制很多,空间更小,很难进行理想的教育实践。
但在合适的时刻,她还是想要做一些事。比如去年九月,校园里开满了桂花,她让学生去赏花,去写诗。讲到史铁生《我与地坛》,作者写到观察蚂蚁搬家这一细微的生活现象,王月给学生布置一项任务,让学生去食堂或者回宿舍的路上,也去观察自己身边的事物。再比如,讲到诗歌“春江花月夜”的时候,她说,“这个景象就像夜晚的路灯下,可以看到一些雾气,一些细微的颗粒。”她描述生活的一些可感知的具体的场景,希望学生们也能具备感知生活的能力。
学生们时常给王月“泼冷水”,他们会说“老师,我看了没感觉”或是“老师,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当然,王月还是要对学生的成绩负责,浪漫的教学只能是一些“点缀”,讲解作文时,她还是会告诉学生们议论文怎么写。
只不过,她和黄修志有同样的观念,无论高校还是中学,语文始终都是一个对于一个人素质要求非常高的学科。老师的素质越高,知识面越广,课堂上能呈现的元素就越多。至少,他们可以把一堂课讲的有趣,变得更丰富、更开放。
就读于南开大学的秘若琳是和黄修志交流最多的学生之一,她所学的专业,研究生只读两年,今年她又将面临一场人生的选择。她想申请博士,但两年的积累远远不够,她给黄修志打电话,说到自己想要延毕一年的想法。以过往的了解,黄修志认为这个学生有足够的学习能力,更重要的是她找到了自己所热爱的东西,作为老师能做的有限,他支持她,理解她。
这些年黄修志放下了一些过于宏大的理想主义,以前他希望每个学生都能够去发声,但这是不可能的。他也理解很多老师不是不愿意去做,更多是因为他们有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
1801班离开了,但故事还在继续,等待发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说不定某一天,它就冒出来了。
前一段时间,王月给黄修志发来一条微信,提起自己在教学中的一件小事。她给学生讲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上到最后,她说希望他们以后也能够勇敢地做出遵循自己内心的选择,坚定自己的理想。接着,她和学生们打趣:“当然大家不能说上语文课上困了,那我就要遵循自己的内心,我就直接趴下睡了。”
王月说完的那一瞬间,脑海中突然闪过大学实习回来开的那次班会,黄修志提到要分清“欲望”和“理想”。“欲望”会让人选择躺平,而“理想”则会让人时刻保持修养和担当。当时王月没有完全理解其中的意义,但就在那一刻,她发现这是一个通俗易懂的好例子。
她继续告诉学生:“当然,如果大家觉得睡觉是你的理想的话,那我也很佩服!”她知道也许学生并不能理解她的话,“但也许过几年,他们才会像我一样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