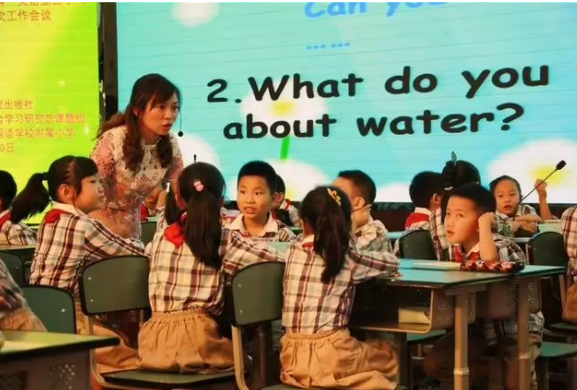2021年3月,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发布疫情期间留学认证的补充说明,指出部分国家的高校和中介以疫情为借口,不断推出各种在线课程,通过降低录取条件、毕业要求或缩短学习时长等方式大量招收中国学生,并声称不需出国就可以轻松获得海外文凭。 (视觉中国/图)
在马来西亚待了两个多月后,徐妍第一次看到那里的海。2022年7月末,趁着学校假期,她和朋友去了趟一百多公里外的马六甲。
徐妍2020年硕士毕业,拒绝了新疆一所高校的教职后,她决定申请马来西亚高校的博士。2022年5月,她从国内前往学校完成博士论文。出发前,徐妍做足了攻略,打算在雨季到来前去看海。
结果,导师给她设定了紧凑的论文进度时间线,旅行是绝对挤不进日程了。
除了应对毕业论文,徐妍还得应付朋友们不时发来的疑惑。有人问,老师上课会讲中文吧?有人调侃,是不是旅个游,顺便拿个博士?一开始,她会认真反击。后来就“懒得说”了,“提问的人其实并不在乎真实情况怎么样”。
新冠疫情以来两年多,出入境人数大幅减少,东南亚留学市场却“火”了。除了徐妍这样为了谋求教职脱产读博的人,多名中介均反映,在职的普通高校教师成了中国学生在东南亚读博的主力。
一名中介描述起他们:大多是学校里的“普通人”,学术能力不足以进入一流高校任职,但也不愿躺平,还想往前冲一冲,拿到级别更高的课题、升到副教授,要么,跳槽去个比眼下好些的学校。
博士学位已经成为在高校系统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在受访的高校教师看来,国内考博竞争激烈,又考虑到自己的学术水平和经济条件,东南亚于是成了一种“不得不”的群体性选择。
“宽进严出”
身处马来西亚,来自国内社交媒体的个性化推送还是精准触发了徐妍的焦虑。
比如,首页推荐里有真假交织的传言:2022年6月,邵阳学院引进23名菲律宾高校毕业博士的新闻发生后,厦门有高校招聘时已经拒收东南亚毕业的博士。
又比如,一些留学中介还在发布“包通过、包毕业、包认证”“两年就能毕业”的宣传广告。
“根本不是这样!”一提起这些广告,电话里,徐妍提高了声调,“但凡QS排名前500的高校,没有能‘水’出来的。”
她正在为达到毕业要求发愁。
2020年8月,徐妍申请上了马来西亚私立高校泰莱大学的博士,学制三年。在最新QS世界大学榜上,泰莱大学排名284位,拿中国高校做参照,榜上最接近的是中山大学,第267名。
疫情之下,徐妍在国内上了一年多线上课程。直到2022年4月1日,马来西亚边境重新开放后,徐妍才前往吉隆坡。这时,她已经在读博二下学期,学校不再有课程安排。
刚结束的一个多月假期,除了短暂的马六甲之旅,大多数时间,她都待在出租屋里,对着电脑分析数据、写论文。首先,她得写好小论文——按照毕业要求,至少得有一篇论文被Scopus数据库(注:全球最大的文摘和引文数据库)收录。另外,博三开始了,毕业论文也得赶进度了。
自从博二开始,徐妍每个月要和主导师、副导师各交流两次,汇报论文进度。每三个月还要向学校上交和导师见面的书面记录。见面次数如果不达标,会被评定为“不满意”,接着,学业警告就来了,连收两次,会受到延期毕业半年的处罚。
在毕业论文上通关,则要完成三次答辩。按照学校规定,入学半年后就可以参加开题答辩,要求是完成论文前三章,包括研究问题提出、文献综述以及研究中采用何种研究方法。
现实情况是,直到2022年3月底,入学1年半后,徐妍才通过了这场答辩。和同期入学的中国留学生相比,她已经算是“学霸”了——直到现在,还有人没参加开题答辩;也有同学被导师要求继续修改半年。
刚过去的9月7日,是徐妍上交论文最重要的数据分析部分内容的截止期限。完成这个小目标后,她将在11月进行中期答辩。要是一切顺利,导师预计她会在2023年3月完成最终的答辩。
“时间太紧了,不可能。”徐妍觉得,导师高估了自己进度。她给自己设定的底线是在2023年内毕业,“三年学制,延期半年还说得过去”。
延期半年不算什么,不少人还没到论文这一步,就被语言关劝退。
张远33岁,是广东一所民办高校的教师,他曾在一家外企当HR,泡在英语环境中办公。而当他入读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当地排名第二的老牌名校时,还是为和导师的交流发愁。
第一次和导师开线上会,张远几乎完全没听明白。导师的英文发音带有浓重的马来腔,吐字很快,“弹来弹去,发音又不饱和”。半小时下来,张远只好不断重复“OK”“I see”对付过去。后来,他和导师改用文字沟通,直到上了两三个月课程适应后,才改回语音对话。
理科大学的入学申请标准不高,雅思只需要5分,甚至比排名靠后的学校更低。但张远发现,5分对应的英语水准远低于实际上课的要求。他向导师提起这个疑惑。导师的回答是,学校希望对学生“宽进严出”,给更多人改变自己学历的机会。
而张远一位同为国内高校教师的同学,由于英语基础不好,实在无法和导师沟通,很快转学去了另一所学校。到了那儿,依然存在交流障碍,最后退了学。
邵阳学院事件发生后,张远愈发觉得这个选择“划不来”,“别人都觉得你的博士是混出来的,只有自己知道,这是认真读下来的”。
不过,回到读博的起点,不论徐妍还是张远,都承认自己其实别无选择。南方周末记者接触到的东南亚读博老师们,体现出某种群体特征——一个学术资质平平的普通人想要当大学老师,可以怎么办?
35岁前毕业,“还有机会进体制内高校”
当大学老师,是徐妍很早就定下的人生目标。她自小生活在大学家属区,那是她熟悉的环境。况且,她是独生子女,老师这个职业有寒暑假,可以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2020年,徐妍从一所普通本科院校硕士毕业。她很快发现,3年前她本科毕业时,可以招收硕士任教的高校,大多把学历要求提高到了博士。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方,硕士要进高校教师岗,基本不可能。
徐妍最终在新疆一所高校面上了教职。不过,校方为了留住人才,要求入职者得签订5年服务期协议。这么一来,就和她的目标有了冲突。在徐妍的规划里,得在30岁前把博士读出来。
“现在这所学校的要求是硕士,3年后最低门槛可能也得是博士。”求职经历让徐妍有强烈的危机感。她拒绝了到手的工作,决定先专心读博。她觉得,既然博士学历已是必需,不如趁年轻一鼓作气,把学历读到头。
与徐妍相似,2021年硕士毕业后,程浩宇在云南某民办高校找到了教职。工作一年,他就体会到博士学历在高校评价体系里的重要性。
例如,在评职称时,硕士和博士的学历差异,会转化为评选时间上的硬性规定。云南省人社厅、教育厅发布的省高等学校教师职称评审条件中规定,博士一入校就可以申报讲师,最快两年,就能成为副教授。而硕士生入校两年后才有资格从助教申请成为讲师,再当5年讲师,才能申报副教授。而评选时间越长,意味着更大的不确定性:要是中间有更年轻、更优秀的同事冒头,名额就可能分配不到自己了。
让程浩宇萌生去东南亚读博念头的,是一位同事的经历。同事的妻子拿到马来西亚高校的博士学位后,被贵州一所公办师范学院作为高层次人才引进,同事则以家属身份由校方分配工作。一个博士学历,解决了夫妻两人的就业。
学历优势也会直观地体现在工资上:每月多发5000元津贴,一年下来,能多6万元收入。
程浩宇所在的系里四十多位老师,2人正在职攻读国内高校博士学位,9人是马来西亚“准”博士,包括他在内的5人都是2022年刚申请上的。读博的同事都是90后,打算趁着35岁前毕业,“还有机会进入体制内高校”。
对高校来说,教师的博士率是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例如,在高校申请成为硕士授予单位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的学位授权审核申请条件中就规定,博士学位教师比例不能低于25%。申请博士学位授予单位需要达到45%。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褚朝晖认为,这与高校的资源分配体系相关。“中国高校发展思路还是把资源向头部倾斜”,申请到硕士点或博士点,意味着生源质量、科研资源、财政拨款都会有很大的提高。
所以,教师申请读博,提升学历,学校都会持鼓励态度。在程浩宇的学校,老师被允许以停薪留职方式出境学习。张远所在的学校也鼓励老师读博,要是能跟学校签订一份取得博士学位后再服务一定年限的协议,学校还会补贴15万元学费。
徐妍将读博视为另一种形式的工作,“等我博士毕业,进高校可以走人才引进,有安家费,不一样是在挣钱吗?”
能力之内的选择
去东南亚读博,在这些普通高校老师的意愿里,曾是排在最末位的选项。
徐妍的首选是考国内高校的博士。回忆起面试经历,她形容为一场“灾难”,“从进去、坐下到出来,5分钟都不到”。
面试官问了她几个问题:父母什么学历、做什么工作;本硕分别是什么学校;高考多少分。说完后,老师们都没吭声,“当时我就觉得完了,凉了”。
而对在职教师来说,在国内读博还有一道障碍,越来越多高校在缩减在职博士名额。早在2015年,南方周末梳理过39所985高校的博士生招生章程,其中5所高校明确规定“不招收”或“原则上不招收”在职博士;13所控制了在职博士比例;3所虽未明确比例,但规定了如“每位导师最多招收一名”的限制条件。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徐志平长期关注学术劳动力市场研究。在他看来,国内高校出于提升博士培养质量的目的,缩减了在职博士的名额。高校教师因此面临尴尬:在职读博需求在增长,供给却没有扩大,甚至还在缩小。
他们于是将目光转向国外。徐妍起初考虑的是澳大利亚。她算了笔账,一年留学的开销需要三四十万,念完博士得花费上百万。
去马来西亚读博,费用在一个工薪家庭的承受范围内:徐妍算的账是,3年学费10万元左右,出国待一年,算上房租,每月生活费大约五千上下,再加上来回机票,要是精打细算,可以把总开销控制在30万元以内。
一家菲律宾留学机构在公众号推文中直白地介绍,菲律宾留学是“应市场而生的产物”,市场主要面对两类受众:需要留学积分申请落户者和评定职称的高校教师。
文中将菲律宾称为极具性价比的选择:“诚然,大学含金量一般,但钱花得真的少,时间短,博导不卡学生,也是完全正规的学历。”
从事马来西亚留学咨询的董林发现,咨询者大多倾向于读一个排名没那么靠前,同时也被中国留学服务中心(下称“中留服”)认可的高校,“他们不求博士学到多少东西,就是用人单位需要这个学位”。
一些看似不符合逻辑的现象随之出现。程浩宇的一位同事最近也决定去马来西亚读博,他硕士毕业于QS排名第21的香港大学。向董林咨询的人中,也不乏英国伯明翰大学、利兹大学等欧美知名高校毕业生,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刷一个”学历。
“杀红眼”的中介
熟悉留学行业的人都觉察到,这股东南亚留学热潮,是在新冠疫情后出现的。按照常规思路,疫情下,出国愈发困难,留学生应当大幅减少才对,而留学中介正通过“无法出境”这点找到了商机。
2020年4月3日,中留服发布了一则说明,表示如果留学生受疫情影响,无法按时返校而选择在线方式修读部分课程,因此导致境外停留时间不符合学制要求的,不影响获得学位学历认证。此前,虽然中留服没有对境外停留时间作明确规定,不过,博士生通常会在境外待满1年以上。
这意味着,疫情下的留学生不用出国,在国内上网课就能完成学业。对在职高校教师来说,无疑提供了一个再理想不过的选择。
马来西亚全球教育服务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留学生的数量是前一年的2倍多,从8876人涨到19202人。其余国家的留学生数量大多在下降,中国留学生占马来西亚总留学生的比例从42%升到了63%。
“高校正经办学,也架不住中介捣鬼。”在董林的感受中,疫情后,东南亚的留学市场一下子乱了套,一些中介为了赚钱,想出了各种招数。
张远最终选择到马来西亚,就有被中介“误导”的因素。当时,中介向他描述,他报名的是“寒暑假博士”。平时正常上班,寒暑假上课,不耽误教职工作,可以“轻松”拿到博士学位。
他直到入学,才发现学校根本没有“寒暑假博士”的说法,只存在全职和在职的区分,并且,在职渠道一般不对外国人开放。
咨询时,还有中介向他推荐过助学班服务,额外支付十多万费用,会有中文助教在班上服务同学。后来他得知,校方从未设置过这样的服务。张远推测,这大概是中介自己请来翻译,再包装成名为“助学班”的产品。
在中国留学生大量涌入的情况下,一些高校也降低了办学标准,放宽名额限制。
2021年3月,中留服发了份疫情期间留学认证的补充说明,就提到了这种现象。说明称,部分国家的高校和中介以疫情为借口,不断推出各种在线课程,通过降低录取条件、毕业要求或缩短学习时长等方式大量招收中国学生,并声称不需出国就可以轻松获得海外文凭。之后,中留服宣布对9所高校加强审查,其中包括思特雅大学,在马来西亚私立高校中排名第二。
不久前,刘妍所在的留学生交流群里就有思特雅大学的学生抱怨,学校大量招收中国留学生,导致博导数量不足,自己已经到马来西亚一个多月了,还没联系上导师,“感觉被骗了”。
马来西亚北婆罗洲大学学院受到更严重的处罚。2022年8月,中留服暂停了这所高校的学位认证申请,理由是学校“涉嫌在疫情期间,针对中国市场突击扩大招生规模,通过在线方式大量输出低质课程”。
“杀红了眼”的留学中介,某种程度上带来了市场的恶性循环。张远在社交平台发布的留学体验视频,不少都在分享学校的“槽点”:博导的学术支持不多,一个老师可能带十多个学生;学生的学术能力参差不齐,能搭伙做研究的不多……
介绍他入学的中介看到了,鼓励他多分享这些真实经历。“不会影响你们的生意吗?”张远疑惑。
对方回答,自己也很恼火——同行们许下“包过”承诺,收取高额费用,搅乱了原本正常的留学秩序。
博士“通胀”
董林在知乎上有7040个粉丝。他开了付费咨询,158元一次,有近五百人购买。单是这项服务,他就挣了七万多。来咨询的人,不少都被中介“骗”过。
有中介承诺,会在入读后提供帮助写作业、指导毕业论文的服务。一名咨询者为此交了二三十万,中介收了费,却只是帮助修改了语法,调整论文逻辑,没法对研究方向提出更具体的意见。
在董林看来,到东南亚读博的高校教师,像是被中介收割的“韭菜”。这不仅意味着他们被变着花招收钱,最终拿到的博士学历,也可能加剧贬值。
他指出,到两三年后,疫情期间增长的东南亚博士们几乎同时毕业,回到国内就业市场,会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即便是不担心就业问题的在职教师,到时的福利待遇也可能比不上如今。
2017年,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徐志平还在华中科技大学读博。他和导师沈红做了一个测算:按照国内高校对学术性岗位的需求,每年需要新招收4.7万名博士。在博士生群体里,大约有一半进入高校,按这个比例,每年有9.4万名全日制博士毕业,才能满足需求。在当时,每年博士的毕业人数稳定在5.5万人上下。论文得出的结论是,国内对博士是“需大于供”。
眼下,这种供需关系已经开始逆转。
徐志平解释,这种变化的发生,首先是国内博士毕业人数将会有大幅增长。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数据,2021年全国共招收博士生12.58万人,在读博士生50.95万人。2022年,博士将继续扩招,按照10%的扩招上限计算,招生人数将突破13万人。
供需变化还有其他因素叠加:越来越多海外博士在毕业后回国;受疫情影响和一流学科评估的浪潮结束,近两年高校教师招聘数量减少;另外,随着应用技术型大学发展,这类院校对教师的能力需求可能也会发生变化,不再单纯看重博士学位。
在徐志平看来,目前,去东南亚读博,对在职教师来说算是高性价比的选择。但如果是为了未来找教职,不论在哪儿毕业的博士生,都会面临更严峻的环境。
徐妍如今庆幸,自己赶了个早。2020年入学时,和她同期入学的中国留学生有7人,2021年增加到十多人。等到2022年初,她的一名学弟想申请泰莱大学的博士,结果等来了学院的通告,由于师资不足,停止招生。
南方周末记者查询发现,马来西亚理科大学艺术专业、博特拉大学管理专业等都在官网发布了停止招收留学生的声明。
“要赶快毕业,赶快出来找工作。”在徐妍看来,就业压力让读博这件事变得“争分夺秒”。至于未来的求职目标,她不敢多想,“双一流高校也好,沿海、省会城市的学校也好,我都没考虑过,能让我进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