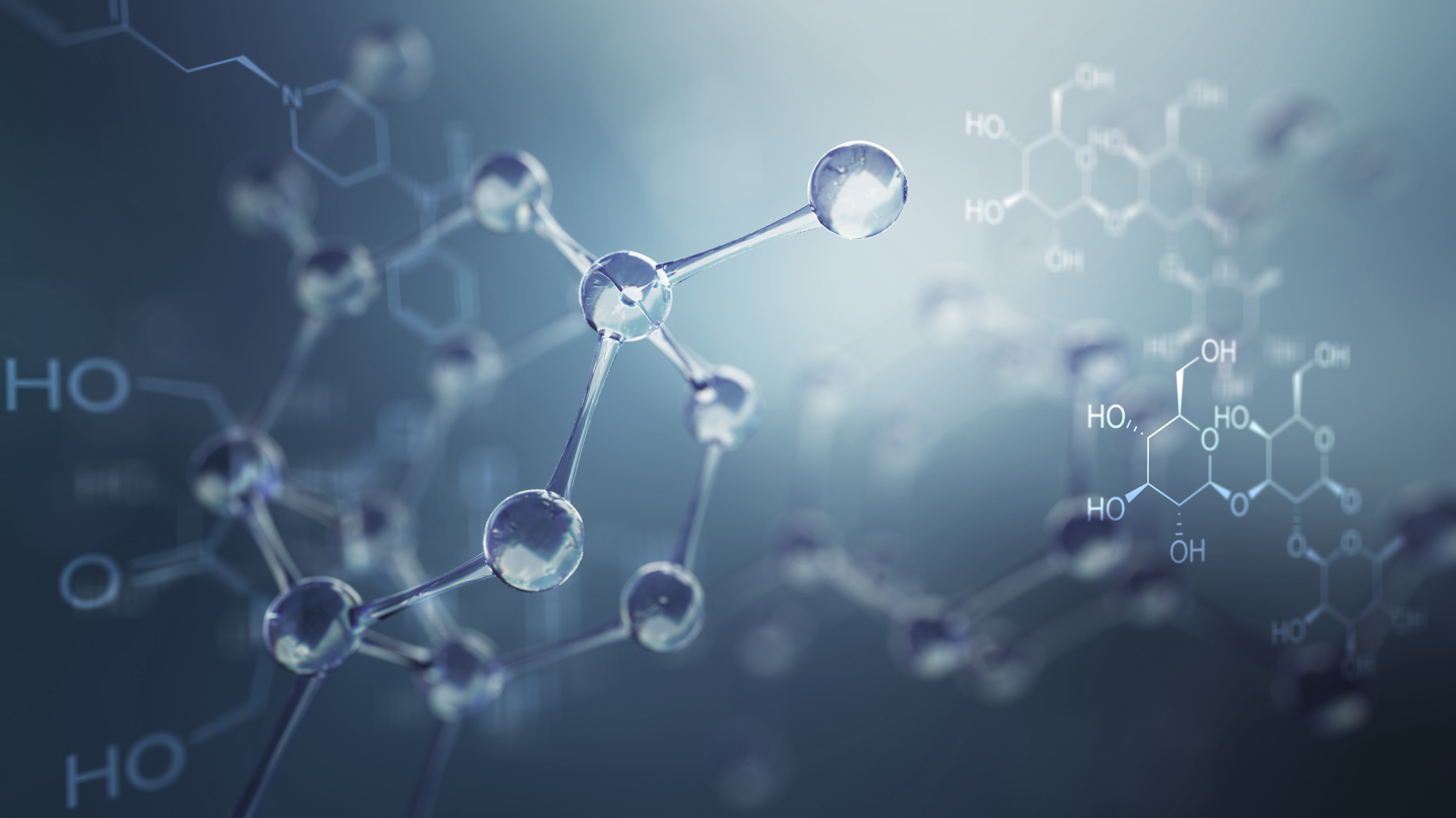钱橙计划通讯员王潇艺吕一含
GapYear(间隔年)是一个舶来词。原是指国外的年轻人在升学或者毕业之后、工作之前,做一次长期旅行,让自己在步入社会之前,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
而在中国,纯粹的gapyear似乎并不存在。社交网络流行一种说法:“中国人的gapyear,是高四,是休学,是考研二战,是考公考编的三四五战。”
读来似乎夸张,但转念一想,确实道出了某种现状:一些逆时而停的人,有人想法清晰,也有人是迫于现实压力——有人起初抱着热情和向往选择专业,却在前辈的经历里勘破某种“真相”,于是决定换个跑道;有人在工作的消耗中丢失了自己,于是打算从头来过;有人曾是“别人家的孩子”,但职场受挫后宅家考研……
在间隔年里,不管是主动或被动选择,年轻人和他们的家庭都面临现实的考验。间隔年之后,年轻人想要“上岸”,也并非得偿所愿。间隔年背后,折射出社会环境怎样的变迁?在他们的间隔年故事里,我们试图寻找答案。
18岁之前的选择
大咕对自己的认知很清晰。她是湖州安吉人,2020年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的园林设计专业——这是学校的王牌,而她要抛弃这个“王牌”,转到科技行业的交互设计方向。
被问到转方向的原因时,大咕像早已准备好似的,流畅地给出四条理由:喜欢且擅长的领域,自己的职业期待,所学专业如何与二者相悖,新专业又如何与之相配。
这些认识,并不是一下子建立的。高三之前,大咕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想的是“赚钱就行”。后来,一直喜欢画画的大咕萌生了要学设计的念头,但高考分数不理想,她就报了和设计“沾边”的园林设计。
上了大学,大咕努力学习,拿到高绩点。她参展国际设计周,也屡次在设计大赛中获奖。但这些努力仿佛只是一种从小培养成的习惯,更多时候她体会到的是消耗感。
大三时,大咕在社交网络上关注了很多建筑行业内的人,感觉90%的人都在抱怨。“会有各种因素限制你的创造力,甚至让你失去对设计的话语权。”大咕说,也是在那时她发现了交互设计这一新方向。
大咕的获奖证书和奖学金证书
大咕准备申请出国,改专业方向,但父母不了解行业,劝她“善始善终”。无奈之下,她在园林设计领域继续深造。
对于职业选择,阿土(化名)也是被动的。她从初中开始就对文学感兴趣,上课时偷偷在书桌里看《水浒传》。她的作文时常拿到高分,也获过省级比赛奖项。同学们常常看见她捧着两本像字典一样厚的书籍翻阅——《全唐诗》《全宋词》。
高考时,阿土超常发挥,拿到全年级第10名。朋友们原以为她会去学文学,结果她报考了南开大学的经济系。
做出这样的选择,不单单是长辈们出于“好就业”的考虑,阿土自己也默许了这次选择。
入学后,阿土一直按部就班地学习,虽然她对课程并不那么感兴趣。从大一转专业,大三考研,大四找工作,每一次选择的十字路口,她都是按着原来的那条路在走。“也是出于一种安全感吧。”阿土说。
18岁以前,刘奕都是亲戚朋友眼中“别人家的孩子”:高中在一个南方县城最好的中学念书,高考时以重点班第一的成绩考进了大学。“父母离异”和“留守儿童”的标签,并没有成为他成长路上的绊脚石,他凭着努力走出了农村和小县城。
18岁时,刘奕顶着父母不解的目光选择了社会学专业。他曾在网上看到社会学相关知识,关于阶层流动、社会公平的概念,一下子击中了他。当时,妈妈说他太单纯,“像我这样出身的家庭,就不应该去思考这些问题,而是去关注一些实际的利益、金钱。”
但大学真正学了,刘奕才发现课程不是这么回事。“老实说,大学基本没学什么东西。一方面也是自己的原因,没有好好努力,混过了大学四年;另一方面也是填志愿的失误,我不太认可社会学的价值。”
如今,刘奕觉得是在为年少气盛的决定付出代价。
想要改变的决定
改变因此来得理所当然。
大三时,刘奕决定考研,但没坚持两个月,他去了湖北一所高中实习。学校的节奏和他的想象大有出入:上岗培训期每天六点不到就要起床,一直工作到晚上十点才能休息。
想换工作,刘奕意识到横亘在梦想职业和现实之间的鸿沟——专业不对口,即使希望当一名英语教师,但211学校的光环也不足以弥补。他再次走回跨专业考研的老路。
父母的想法并不统一。刘奕父亲初中学历,思想传统,曾希望儿子早点出来工作。他担心儿子在激烈竞争的大环境下无法顺利上岸。母亲则比较支持刘奕的选择,一方面她希望儿子离家近些;另一面,她觉得儿子口才欠佳,可能无法胜任高中老师的职位。
做出改变决定之时,阿土已经在一家商业银行里工作了将近一年,换到了一个管理岗——那意味着,她的工作能力得到了领导的认可,职业发展看上去稳定又清晰。在这个时候,她提出了离职,并向领导透露出继续学习的想法。
领导反问她:“读研两三年出来,你不还是要找工作吗?”她仔细想了想,没有动摇。
阿土决定辞职,是因为做了一个梦。梦的具体内容她记不清了,但她记得当时醒来就很难过,觉得文学好像真的要离她而去了。
在那之前,因为工作饱和,她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看书了,想不起上一次拿的是什么书,读到了哪儿,每天累得就只想躺着。取而代之占据她脑袋的,是一切跟经营、财务、盈利,还有她的金融产品相关的想法:“怎么让客户的公司和自己的银行都能赚到钱?”
2021年8月份,阿土正式辞职。认真思考了一段时间,她决定脱产,考文学系的研究生。
而对于大咕来说,留学的那一年,反向推动了她要转行的想法。她在伦敦大学的巴特莱特建筑学院深造,即使在全球数一数二的建筑学院,她也没能找到对于园林设计的热爱。去年十一月结束在国外的学业后,她没有犹豫,果断开始了居家学习的生活。
这一次,父母没有再说什么。大咕花了半年时间,在国外的网课平台上系统学习了交互设计相关课程,并积累自己的作品集。
在暗房里洗衣服的人
无论目标是否清晰,最后能否上岸,间隔年期间,他们能清晰地感觉到与同龄人的鸿沟。
在间隔年期间,大咕几乎断绝了和外界的联系。她很少和朋友见面,害怕别人会问她“怎么还不去工作”,“我感觉有好多双眼睛在盯着我,好像大家对我有什么期待来着。”
这一年,大咕始终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为了给自己建立秩序感,她每天坚持做一些事情:看书,打半小时羽毛球或者游泳,在网上学习法语。
父母支持大咕的居家决定,每个月妈妈会给她转钱,但是近三个月来,她并没有收,“他们会给,但是我难受。”她通过知识付费赚了一点钱,而且尽量地压低自己的花销,每个月基本生活不超过一千块。
毕业后的这个暑假,对于刘奕来说有点难熬,高中时期的同学上岸的上岸、保研的保研,大家都有光明的未来,“我一个‘211’毕业的还在家里蹲苦苦挣扎,会被看不起吧。”
刘奕的母亲是一名幼师,暑假幼儿园放假,便在家负责安顿好刘奕的吃住,包揽了煮饭洗碗所有的家务活,还会给刘奕切苹果加餐,夸张点来说,就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刘奕却觉得不是滋味,“一个成年人至今还没有经济来源,还有成为妈宝男的倾向。大概我都不能接受这样无能的自己吧。”情绪上头时,他也会回怼母亲:“你以为我现在出去工作赚不到钱吗?”
不仅如此,还有面对未来的忐忑。刘奕坦言,高考时考上“211”院校有运气的加成,如果不是高中学校的严苛管理推了他一把,他大概很难自我驱动,考出小县城。
“以前觉得自己是个‘小镇做题家’,现在没有了学校的管理,连做题都不会了。这一点太要命了。”刘奕说。
阿土也怀疑自己能否考上。这几年,考研竞争越来越激烈。今年春天,在她所加的一个考研交流群里,一个考了397分的女孩子每天都焦虑着是否能进复试。而在几年前,复试线长期保持在360~370分左右。
阿土在出租屋内的书桌
阿土此前已做好“二战”的准备。她在镇上租了房子,白天去县里的图书馆自习,晚上在家里学习。从高中开始,她就有一点“考前综合症”,容易焦虑,频繁失眠。为了调整睡眠,她买了睡眠贴,还有口服液,甚至还喝了一个月的中药,而这些只给她带来了心理作用,实际用处不大。
曾经有人将考研比喻成在黑暗的房间里洗衣服。那个洗衣服的人,看不到自己洗到什么程度了,但是一刻也不敢停下来,直到灯打开的那一刻。这个比喻,很像每一个在间隔年停下来,然后重新抉择的人。他们谈及“gapyear”以后,未来几年的目标,大多指向一个更理想的职场起点。
刚刚过去的夏天,1076万的毕业生数字创造历史新高。眼下,招聘季又轰轰烈烈地开始了。阿土和刘奕还在家中复习,大咕准备奔赴上海,加入今年秋天的招聘季。她琢磨着,自己是不是该去练练演讲与表达,好在这个招聘季能有所获。
一切还在继续,一切都是未知。
(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