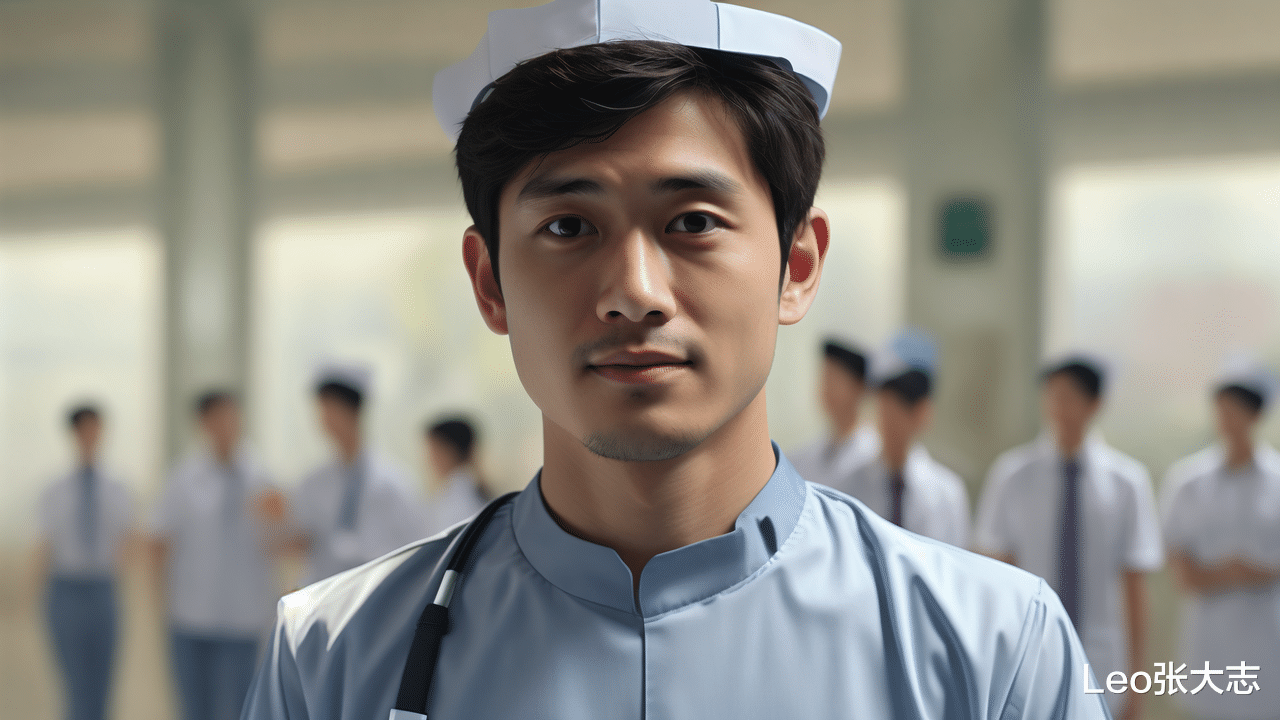吉雅是我在大学里最好的朋友,直到他退学前我们在校园里几乎形影不离。他已经退学十个月了,现在的身份可以是银匠或者牧民,但我更想形容吉雅是一个坚持“做事”的人。
他逃离了自己所厌恶的“托管式大学教育”,带着还未消耗殆尽的创造力,回到眷恋的牧区草原,靠一门手艺吃饭。过年回家见到吉雅时,他似乎已经完全摆脱了上学时的那种苦闷。
这是一个鄂温克牧民青年在当下寻找出口的自救之旅,也是我曾畅想过但未能下定决心作出的那份选择。
上学
三月份,自从我回到学校后便开始忙碌着关于毕业的琐事:写论文、补学分、准备那些还未通过的考试,偶尔打开邮箱看看投递的简历是否有反馈。尽管做着多份写写东西的兼职,偶尔会出去放歌DJ一下,目前是饿不死自己,且很快乐。但一到毕业这个节骨眼上,传统思想还是开始作祟,每天反复问自己:“要不还是借着应届生的身份,先找个稳当班儿上比较好?”
反观舍友与同学,基本上还是考编考公考研三件套。有人拿到了他想要的,每天喜笑颜开;也有人满脸阴郁地反复翻看考试资料,秉持着逢试必考的心态持续坚持,持续崩溃。
于是在毕业学期刚开始的第二周,有人疯了,开始吃上药,但不是那帮考来考去的人,而是我,一个陷入焦虑的敏感人。
在接过劳拉西泮和氟西汀后,大夫告诉我别紧张,吃一段时间就能好了,我盯着这几个药盒苦笑,脑中突然回闪了一个画面,是吉雅面无表情地对我说:“在这学校继续待着,早晚得病”。
吉雅跟我都来自呼伦贝尔的鄂温克族自治旗,尽管有一些共同的朋友,但在大学入学之前我俩从未见过面。新生报道那天,我们互相对视了一眼,仅凭对方的外表便各自在心里默认“这小子能跟我玩到一块去”。就这样,我们一块五脊六兽地在大学校园里混日子,靠着酒精、电影和音乐打发时间,蹲监狱似地数着还有多久能毕业。
你若问我们为什么如此讨厌自己的大学?也许是能力或者运气不太好,考来了一所偏远城市的二本,在这儿的所有文娱生活都是自娱自乐,而几乎每一所偏远城市的二本学校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管理严格。也不知为什么,我与吉雅常常凭着心情做事而背上处分或是警告:校园内禁止饮酒、张贴在宿舍墙上的海报总是会被勒令撕掉、周末与节假日也不允许夜不归宿等等。总之,大学生活对松散惯了的我俩来说苦不堪言。
记着念预科的第一个学期里我无数次跟父母闹翻准备退学,那会儿一心想去学纹身,以为有门手艺能养活自己,肯定要比念书拿文凭更靠谱一些。当家里对我的行为忍无可忍之后,决定停掉我的生活费,在月中旬兜里仅剩不到二十元的情况下,我选择向家里服软,好好上学。
那段时间吉雅常常劝导我再坚持坚持,可能习惯以后就好了,没想到在第二年的同一段时间,他向学校提交了休学一年的申请,这么看来他也没能习惯。
当时吉雅选择休学,对我来说有点突然,但细想也早有铺垫。在学校呆了一年后,有很多事物让我俩感到难受:随处可听到短视频外放的声音,宿舍楼道半夜总会有人连麦打游戏乱叫。在这儿的大部分人每天把自己扔在短视频与游戏中,然后等到快要毕业时参加某些体制内工作的考试,或是为了不早早参加工作而选择考研,他们基本上都有个相似的路径去走,并且有很多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
环境对人的消耗如同温水煮青蛙。我和吉雅并不能评价他们所选的道路是错的或是无聊的,但很明显是我们非常抵触的,每每谈到这些,我们都说要么干脆别念了,但等到第二天酒醒之后还是按部就班地赶早上课去。那段日子就是这样无限循环着,我们痛批现状,忏悔反省,然后又继续上课,直到吉雅休学。
休学那年假期,我和吉雅在牧区一起游荡
休学
吉雅休学后的选择是去学门手艺,他多次和我提到过要成为一个“做事”的人,而学校的环境似乎会削弱他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于是他找到了家乡的一位银匠拜师学艺。
吉雅跟我说,当他第一次看见银锭在喷枪射出的火焰下缓缓融化,犹如覆盖着白雪的伊敏河突然在骄阳的照射中解冻直至清澈,那感觉就像是在短短的几分钟内亲眼见证了寒冬与暖春的交替,火焰昂扬的生命力在这一刻被完全的体现了出来,并且最重要的一点是,这熊熊火焰由银匠亲手操控。
这个过程让吉雅眼前一亮,而用金属器件儿敲击打磨半成品的过程更是挥发力量与专注细节的挑战,等到一件饰品真正完成了从0到1的进程而摆在吉雅面前,他觉着工作台上每一处事物,都要比课堂上老师讲授的内容更具吸引力。
在师父手把手指导下,吉雅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件作品,他下定决心要把“做银饰”这件事好好做下去。他发觉,世界上可能很少有比将脑中的想法转化为手中的实体这种事更爽的。吉雅不再茫然于学习究竟有什么用,他找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学习模式:去学习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去学习归置的自己想法,让它们更加具体。
在学习银器制作的同时,吉雅也开始更多去了解自己的家乡与不同部落的文化,进而与自己的作品相结合。内蒙的大部分银匠主要制作的是一些带有游牧民族特色的饰品,常见于服装以及布匹上的花纹与传统的图腾符号。吉雅想从这里跳脱出来。因为相同的饰品已产出太多,如果每天都做着别人已经做过的物品,时间长了也会感到索然无味。在他的大部分作品中,游牧民族和牧区的文化符号往往只是作为部分元素插入,而非作品的主体。
吉雅做的饰品
图一是吉雅画的马,对于他来说是“精气神”的象征
经过一年的学习和沉淀之后,吉雅与我一同踏上了回学校的火车,在出发的前两天我问他还想不想回去了,他开玩笑着说:“我想彻底退学。”
那是2021的下半年,我们依然过得苦闷,吉雅在与金属器械打交道的这一年中也算是得到了磨砺,不再抱怨环境与周边人的行为,只单纯地为自己而苦闷,幸好还有酒精的陪伴,能让我们接连不断地得到暂时的麻痹。不过这次返校之后,吉雅请假回家的频率越来越高,我甚至感觉他在学校的时间远比在家待着的时间要少,但也好在没有因为落下太多课程而被勒令退学。
紧接着迎来了令人无比头痛的2022,由于疫情的反复出现,学校不断推迟开学日期,于是我们就在家整整待了大半年,在这期间吉雅和休学那年一样,按部就班地往返于牧区草原和城区的银饰工作室之间,日子逍遥自在。从我的视角来看,他似乎将牧区生活当作一种收集能量的方式,与草原、河流、牛羊相处,能让他无数次沉思这世上的万事万物究竟是如何链接到了一起,等再回到工作台前面对着尚未完工的半成品,他总会有新的想法去推翻之前的做工。
在他下工后,有时我们会约着到伊敏河旁边坐下喝酒,像在学校时一样,我们手里端着啤酒罐时面前必须有水,哪怕是景观池塘。当夏夜的晚风拂过吉雅的脸庞时,他常常会顺势往后一靠,说上一句:“还是在家待着舒服。”
退学
在熬过那颠簸的三年之后,校园生活不再有封控,吉雅也难再凭着古怪的疫情理由请假回家。当我俩又一回坐到校园的池塘边喝酒时,吉雅向我讲述他做了一场怪异的梦:
他梦到自己站在家门前,用双手挖了一捧脚下的土壤与草,大声向远处正在把行李装上车的母亲索要一个布袋,吉雅也不知道为什么此时此刻自己要把手里的土装起来,环顾四周后才看到牛棚羊圈早已空空荡荡,家里的所有人都在把屋里的家具搬到院子,父亲见吉雅僵硬地站在那里,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描述着未来搬离牧区草原的生活将会怎样……
“可能这一天真的快要来了,三年?五年?我不知道。”
吉雅用很平淡的语气说出这句话,然后低声啜泣。音箱里开始播放着走马电台的《夕马牧人》,吉雅很喜欢这首歌,每次听到时都能想起令他记忆深刻的那个下午:哥哥牵着一匹马走在他的前面,夕阳的光线均匀的洒在他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马鬃的颜色随着太阳的高度变化由亮转暗,二人就这样无言地前行,好像所有的话语在阳光下都显得不再那么重要。
对于吉雅来说,牧区草原是身体中无法割去的一部分,但他深知自己的牧民生活可能不会持续太久:矿场开采所导致的污染,始终影响着吉雅从小生活的那片草场,饮用水变质、牲畜死于肺病,当风沙吹起时甚至连太阳都被牢牢遮住。种种问题不得不让当地的牧民为生存作出选择,或是卖掉牛羊马匹搬到城区生活,或是迁徙到远处寻找合适的草场,告别世代生活的土壤,一切重新开始。
应当抓住有限的时间缓慢地与草原告别,这也是吉雅决定退学的一大原因。
吉雅所眷恋的是故土草原能够为他带来的坦然心境,牛羊从出生到被宰杀的轮回、夜晚的星河能从天空流淌至屋后的水坝,太阳缓缓从绿色的地平线升起,平等地将阳光分给每一颗花草,这些事物足以将一个人的世界完全填满。在自然中所构建的规则从来都是以真切的生命力为基础,它是随机的,是经验也是传承,所以在这片土地上你遇到的问题不需要任何准确的答案,哪怕在问路时,你也只需凭着对方语调的高低和尾音的长短,来判断他手所指向的目的地距离究竟要有多远。
而在城市里,大部分事物包括人群都要进行合理的规划,要准确要细致。我们所经受的教育体制不但要我们记住每一个标准的答案,还须要我们为自己找到准确的定位,这些事情常常与吉雅为自己建立的观念而冲突。吉雅不需要准确的答案。
退学的过程毫无波澜。吉雅的父母并未作出阻拦,他们认为他只要想好自己要做什么就可以,况且儿子的生活是自己的,并不应该过多去干涉。而学校这边,办手续的流程也十分顺利,令吉雅感到好笑的是,平时对他指指点点的班主任,在给吉雅签署退学申请书时喜笑颜开,好像特别高兴。
告别了学生身份之后,吉雅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当然是想办法养活自己,吉雅花时间认真地精进技术,并且开始了订单制的工作模式。客人将自己对于饰品的想法讲给吉雅,他再根据他们的想法填充进自己的风格,一件儿做完了就立马还有下一件儿。创造的乐趣往往大于赚钱,当订单达到一定数量时,他会选择回到牧区“充电”一段时间,也算是种良性的循环。
上个月的某一天,吉雅到我家里来喝酒,暖气烧得人浑身燥热。打开窗户,室外零下三十多度的冷空气吹进屋子后变得像夏夜温柔的凉风,我们闭上眼睛仔细让身体抓住这丝凉意,仿佛穿越到了夏天的伊敏河旁,吉雅说这便是“seyoreousau”,这个鄂温克词语直译过来的意思是“舒适的”,如果进一步延伸表达,它更像是描述着河水与晚风在一同流动在眼前。
这也可以形容吉雅当下的状态:像缓缓流淌的伊敏河水。
于我而言,吉雅迈出了我未能迈出的那一步。我可能需要这份文凭,可是又讨厌拿到毕业证之前的种种烦心事儿,十分拧巴。
大学带给我的苦闷始终不能消散。在这种不舒服的日子里,我也在尝试着作出一些选择,去减轻这些情绪,比如把注意力放在寻找更好听的音乐,或是想一想有什么好玩的故事可以写写。虽然还未进入到“seyoreousau”的状态之中,但做着让自己能享受其中的劳动,起码不是个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