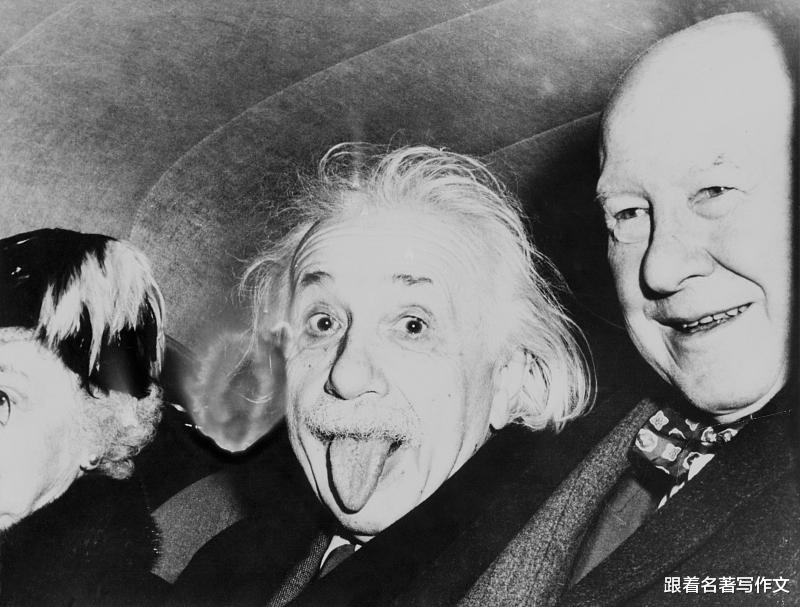除了教育行业内的公司不好过之外,家长们无处安放的焦虑也随处可见。
在一份头部教育公司的客服电话录音里,一位女性家长主动给教育机构提建议,“周末孩子不能上课的话,你们培训我们家长,我们再回去教孩子行不行?”
她有些哽咽地说。“请你们提高学费,只要你们能撑过去,我相信这种局面不会持续太久,也许一年就过去了。”
现在摆在教育机构和家长面前的问题是:这种局面是一年就过去了,还是会继续持续下去?
大部分教育机构,相信是后者。
7月27日下午四点多,好未来创始人、CEO张邦鑫向员工说:“我们这些机构配不上我们的客户了,我们公司也配不上我们的高管和干部了。”
张邦鑫说这话,大概率有一种命运无常,难以改变的无奈感。
2010年,好未来在纽交所敲钟上市。到今年年初,好未来市值一度超过550亿美元,曾最高聘用超过7万人在好未来全职工作。
高楼起得快,但坍塌得也快。
7月27日,在一纸文件下发后,新东方市值较今年高点跌去90%,好未来跌去95%,教育行业从香馍馍到避之不及的“瘟神”,前前后后只用了5个月。
张邦鑫在内部讲到裁员时,带着点内疚,“裁员是肯定会裁员的。没有需求的业务肯定会被关掉,相应业务上的员工能内部转岗就先转岗,不能转岗的,公司会给予赔偿。”
根据好未来最新一季的财报来看,好未来90%以上的营收都来自中小学教育培训业务。这次裁员,既是必然,也是某种无奈。
高途教育在这场风波中,也难以置身事外。
在“双减”意见下发的第二天,高途教育创始人陈向东就召集管理层开会,定下了裁员指标。
全国13个地方中心,在8月1日前完成关闭,只留下郑州、武汉、成都三个辅导老师中心,每个中心平均上千人,涉及员工人数上万,这相当于高途三分之一的人会离开。
一位高途职业教育中层管理人员在对团队宣布裁员消息的时候,两次哭了出来。
这场意外来得太快,以致于没有得到任何缓冲的可能性。
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中小学教育得益于疫情蓬勃发展,仅仅在一级市场的风险融资规模就超过500亿元,超越了过去十年的融资总额。
而现在,投资人、业务、家长、孩子,多线并行焦灼,难解难分。焦虑的不仅仅是教育机构,还有那些“望子成龙”的家长们。
根据规定来看,学科类培训机构都得转为非营利性机构,收入只能用于弥补成本,盈利不能用于分红,只能用于自身发展。
单这一条,就限制了教育行业的任何可能性。
更令人担忧的是,今天是教育,明天会不会就是其他行业?
教育行业受到波及,蝴蝶效应也开始显现。
首当其冲的,就是各个信息流平台的广告收益。去年暑期,单是猿辅导一家在字节跳动一天的广告投放额就超过3000万元。
而一位长期与字节跳动合作的广告人士表示,年初字节的教育类广告有约70%的收入都来自于中小学业务。
除了字节跳动之外,其他信息流平台诸如百度、腾讯的广告收入,教育类都是不容忽视的关键。
根据一些机构的预测,2023年中小学线上线下的市场规模将达到上万亿元。中小学教育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家长们对于应试的焦虑感和内卷。
而素质教育则无法解决需求端的根本需求,如今供应被彻底打乱,应试教育所面临的焦虑和内卷却依然存在,这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家长们可能找不到突破口。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学科培训从明面上转到私底下,这其中多出来的成本,最终还是会转嫁到家长自己身上。
需求得不到释放,需求就会消失吗?还是说,需求会以另一种更为“隐秘”的方式存在?
我更倾向于后者。
而成人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市场,则远远不及中小学教育。
根据Frost预测,不提供学历的职业教育在2022年能够增长到2000亿元的市场规模。而艾瑞咨询的数据则显示,2020年素质教育营收规模突破4200亿元,这两个市场加起来,也只有中小学市场的一半多。
说到底,教育不应该商业化,但为什么教育就商业化了呢?市场,市场是很重要的,有需求,才会有供给端。
反过来,当供给端足够大的时候,也会反过来刺激需求端。
这就好比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当孩子的学习成绩提高是解决未来出路的唯一办法时,家长们比拼的就是谁家的孩子能够在学科培训中步步取得先机。
借用一位业内人士的观点来说就是:校外培训机构发展之所以会如此迅猛,本质上还是校内教育评价标准过于单一。
一切以考试成绩来“论资排辈”,这自然就给校外培训提供了许多野蛮生长的土壤。
竞争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而良性竞争和恶性竞争,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其结果往往就是天差地别。
当整个行业理智的人都在癫狂时,这个行业的灯或许就该关了。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