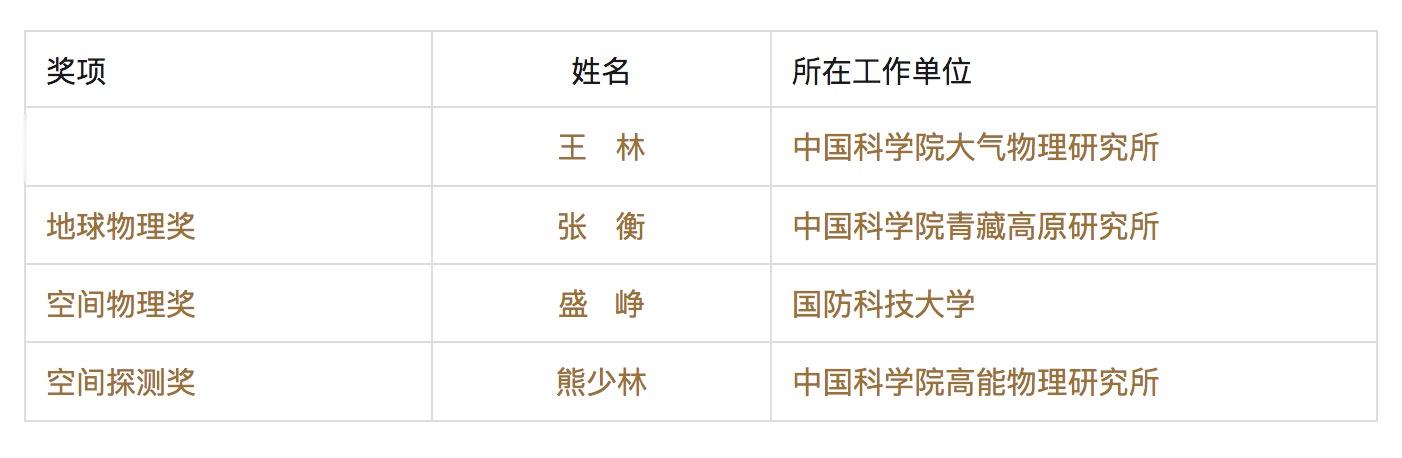原题
走过独木桥
——往事一二三
作者:黄慧
上学,似乎是每个学龄儿童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我们这一代人的求学之路却走得曲折坎坷。重回校园之前的那段人生,是我们独有的难忘经历,几十年过去了,依旧历历在目。
遭遇文革
童年,多么美好的岁月。有人说童年是金色的,也有人说是粉红色的,或者天蓝色的,总之是甜蜜的,无忧无虑的。而我的童年则以1966年为界,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颜色,我的性格也随之有了明显的变化。
该上小学那年,由于生日晚于法定开学的9月1日,我被通知因学校满员要过一年才能入学。两周之后因一人转学,我才得以赶上末班车。谁料到,这竟然预示了我坎坷的求学之路。
小学三年级以前,作为祖国的花朵,我很快乐。从三岁起我就上了全托幼儿园,小学又上的寄宿子弟小学,生活规律、简朴、平等。戴上红旗的一角,左臂两道杠,我是学校队旗护旗手,右手举过头顶,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
不怕艰难,
不怕担子重……
这首少年先锋队队歌直至今日我还记忆犹新。我们是红旗下成长的新一代,努力学习,长大为建设祖国做贡献,这是我们童年纯洁心灵的理想。我每周日晚乘校车回学校,周一到周五住校,周六早上回家。短暂的周末全家团聚,在中山公园或北海公园荡起双桨,再来今雨轩和仿膳午餐,到北海五龙亭码头乘坐少年先锋号游艇,去看身穿小海军军服、假装不认识我们的哥哥……童年真是金色的。
三年级快放暑假时,教师食堂一反常态地拉上了窗幔,透过窗幔的缝隙可以看到里面贴上了许多大字报,有的人名上还用红笔打了叉,同学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一种不祥的气氛逐渐蔓延开来。
八月中旬,快开学了,我正在家赶暑假作业,却收到学校来信通知,说因子弟小学搞特殊化,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温床,开学日期被无限期推迟。没想到,从此学校竟被永久关闭了。
一天下午,我从外面游玩回来,见院门大开,两个红卫兵守在门口,凶巴巴地问:“你要干什么?”我刚要说“我回家啊!”保姆“妈妈香”一把把我拽出院门,说现在不能回家,让我再去玩会儿。(注:据保姆说“妈妈香”是我两岁多时给她起的名字,因为她名字里有个“香”字,以区别于我的妈妈。)
天快黑了,我的肚子开始叫起来,回家推开院门的一刹那,我惊呆了!院子里一片狼藉,被撕碎的相片纸片散落一地,还有破碎的玻璃与瓷器,我小心地踮着脚,避免被扎到。屋里被翻得乱七八糟,比电影里看到的镜头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被吓得大气不敢出,默默地帮助爸爸妈妈收拾屋子,好整出睡觉吃饭的地方。从被抄家的这天起,我的童年褪去了原有的色彩,变成了灰色。
由于学校被解散,我不得不插班就近入学,在红小兵们的指指点点下变成了一只受了惊吓的小兔子。家里的卫生间和厨房都被拆毁住了人,院子里搬进了五户红五类,我们只能用街上的公共厕所。而每次用厕所对我来说是一种煎熬,那里没有隔断,若是碰上红小将在那儿“狗崽子”“狗崽子”地指桑骂槐,我只能落荒而逃,经常要来去好几趟才能上完厕所。这种惊弓之鸟的情形一直持续到初中。
初一下学期接近期末的一天上午,班主任董老师挺严肃地让我下午课前去她办公室一趟。我吓坏了,不知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接下来没心思上课,一直在反省中。下午我战战兢兢地找老师,眼泪随时准备流下来。董老师却说:“学校要在咱班发展团员,这是登记表,你填一下,明天交给我。”我完全懵了,这怎么可能?怎么是我?难道真的因为我是三好生(守纪律,学习好,又是校队队长)?就这样,我将信将疑地成了全班第一名、全年级第三名团员,我还真没做好思想准备应对这种身份转变。
初二时,蔡老师成了我的班主任。她是蔡锷将军的长孙女,正直善良,是她改变、重塑了我,使我对人生重新燃起了希望。班上有生活困难的同学、也有出身不好的同学,她都一视同仁。她不仅教我们中文,也教我们如何做人,这对我们这一代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半大孩子尤为重要。我逐渐变得开朗自信,并慢慢走出阴影,渐渐形成了阳光乐观的个性。我积极参加班级和学校的活动,还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全国团代会。去年蔡老师在东京病逝,我们班上好几位同学都发去了情感真挚的唁电,讲述了蔡老师当年在逆境中对大家的关爱和帮助,每个人都认为蔡老师是我们生命中重要的指路人。
我们是文革后第二届高中生,,学校逐渐恢复了秩序。我们班上的同学是从六个初中班择优录取的,学习气氛挺浓,据说以后要直接升入大学。我们的班主任王老师是“文革”前复旦大学数学硕士,这在当年是很少见的。王老师教学不仅有条理,逻辑清晰,而且板书极漂亮。我常常在听懂课堂内容后偷偷学王老师的硬笔书法,有一次还被王老师发现不专心听讲而被点名回答问题,好在我已经会了。
一次上制图课,回家我三下两下就把作业做好,爸爸瞥了一眼,问我是否愿意用鸭嘴笔画一张工程师那样的图,他拿出专业制图盒及绘图纸,教我怎样给鸭嘴笔挂墨,怎样按制图纸上的小格画比例,我的兴趣大增!第二天,我不但交了一张普通制图作业,还得意地交了一张虽然简单但貌似专业的真图纸!数学是我中学最喜欢的学科,制图大概和绘画也是相通的,以至于后来高考的第三志愿我填的是北京钢铁学院机械系。
不料,时至1973年夏,风云再度变幻。文革末期的又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我们高中毕业后失去了升大学的机会,求学之路又一次走不通了。
知青岁月
1975年1月,我高中毕业了,升学无望,当兵、留城也无路,只能去插队,别无选择。在京郊插队,我们比起其他人,还算幸运。春节后,我和三位高中同学八位初中校友一起来到北京顺义县南彩公社杜各庄大队,成为一名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
我曾看过一本回忆录,书名为《南彩风暴五十年》,是当地农民游击队与还乡团斗争的回忆录集锦,故事就发生在这里。1962年在这里还拍了部电影《箭杆河边》,写地主暗中散布谣言说国民党要反攻大陆,社员们在队长领导下与其斗争的故事。这电影我没看过,但一想到就要一睹箭杆河的风采,我还有些小激动。这条著名的箭杆河就从我们村里流过,是潮白河的支流,全长27.5公里,流域面积236平方公里。在插队期间,我还因为算是壮劳力参加了治理箭杆河的挖河劳动。
虽然从小衣食无忧,“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但自幼集体生活使我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体育锻炼也培养了我不服输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上中学时每次批评与自我批评我都被批评有“骄娇二气”,我心里其实很不服气,只接受其一,不接受其二,别认为家境好容貌好就必定娇气,不信拉出来练练,看谁更能吃苦!干农活,很累,我切身体会了面朝黄土背朝天、一个汗珠摔八瓣的涵义。但我不怕吃苦,何况小命还捏在人家手里。
除了个别农活没干过,几乎女社员能干的活儿我都能干,挣女社员的最高工分8分,到年终分红时我还分了三百多元,这是我有生以来自食其力的第一笔收入。
挖河是重体力劳动,河泥既粘又重,铁锹要像切年糕那样垂直切下去,时不时还要蘸蘸水,好洗去黏在铁锹上的河泥。河堤大约呈25至30度角,要用独轮车把挖出的河泥推上去。河泥含水量大,很沉,推小车很费劲儿。而且独轮车不好推,开始我推不好,接连翻了好几次车。那时常说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炼一颗红心。心红没红不知道,但晒黑了,体力好了,饭量大了,连我自婴儿时就有的经久不愈的顽疾湿疹也因粗茶淡饭而不治自愈了。
有一天广播电台记者来采访,报道知青铁姑娘云云,让我在河堤上念报纸还录了音,回家后在收音机里听到了新闻采访实况录音。这是我第一次在录音新闻中听到自己的声音,挺新奇,也挺兴奋。爸爸妈妈和邻居们也为我高兴。
当过知青,才知农民不容易,更深切体会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涵义,现在遇到我丈夫老唐吃饭剩好多米粒在碗里,我总要批评他欠缺插队这一课。也因为当过知青,伺候后院菜地时也总自夸自己是“农民”出身。
告别学校来到农村,除了下田劳动,出工之前给社员读报纸、在队部出板报、给广播站写稿之外,我还当了一学期小学代课教师,负责两个不同班级的语文、算术和自然课。这算是发挥了一些与知识有关的作用。那时说80年代末将实现农业机械化,用联合收割机收割小麦,我很兴奋,脑海里憧憬着那幅景象。当然也讲给了孩子们听,让他们写作文,因为那是农业发展的未来和孩子们的明天。
因为要出板报,我从家里带了两本板报图案。晚上闲的无聊时就随便画两笔。附上两张极富时代特色的板报画。
有个小社员拿来她的一寸照片让我画,这便成了我的第一张照猫画虎的“临摹”。后来还照我高中同学和从未谋面的五姨的照片画过。想家时也画过妈妈。报纸上的工农兵版画,也被我拿来当教材,涂涂画画和看小说成了我插队时的全部业余生活。当然,也曾跟过广播电台学习英语和日语。
插队近两年的时间里,我正好经历了动荡的1976年。
7月28日凌晨3时42分,睡梦中的我被惊醒,地震了!我赶紧叫醒两名同屋插队校友,并呼唤房东老乡一家人。这是上世纪世界上最惨重的里氏7.8级强烈地震,震中在唐山,北纬39.6度,东经118.1度,震源深度16公里,距北京仅三百多公里。天亮后我们出了大约半小时工,就因大家心神不定而收了工。我在村里走了一圈,万幸,所有倒塌的墙壁都是往外倒的,没有人员伤亡。
恍惚之中我走到了村口,长途汽车站就在旁边,我忽然有了强烈冲动,要回家看看家里人怎么样了。好在钱包随身带着,可以买票。等了一个多钟头也没有车来。这趟长途车往返于平谷和东直门之间,每个钟头都有一趟。继续等,车还是无影无踪,倒看见几个从平谷方向走来的人,他们说这条公路下面是沙丘,公路被震裂了,不通车了。我想了一下,决定也和那几个人一样走到县城,坐火车回京。
从杜各庄站到顺义县城大约20里地,好在都是平地,初中一年级拉练时走的比这还远呢。我以亚急行军速度向县城奔去,中途真的看到了公路上的大裂缝,有1至2米宽,40多米长。我不敢停留,继续往前走。这时,低沉的雷声响了起来,下雨了!我拿出兜里仅有的手绢,把四个角分别打个结,当成小帽戴在头上,其实一点用也没有,但这却是我唯一能做的事。
终于到了县城,顺义火车站里已经聚集了不少知青,可是火车不发车,因为铁路有可能因地震而变形,造成出轨翻车事故。知青们都焦急不安,外面下着大雨,回家无车,回村也无车。过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有列车进站了!好心的列车员阿姨招呼所有知青先上车再补票。列车呼啸着驶出了顺义县城,迎着暴雨向45公里外的北京站进发。
出了北京站,大雨滂沱,我没有伞,只能像百米冲刺那样跑到公交车站,有好心人让我分享她的雨伞。下车后又是一路狂奔,见到人们都躲在街上的简易地震棚中,有人干脆打伞坐在凳子上,这种情形一辈子再也没见过,终身难忘!
三个月之后,1976年10月6日,平地惊雷,“四人帮”被一举粉粹了!10月21日首都150万群众举行了盛大庆祝游行,京郊的社员们也同样兴高采烈,觉得生活有了新的希望。
走过独木桥
1976年11月,我被招工回到北京,成了新华印刷厂铅印车间的一名工人。
我们车间有四台西德进口的大型印刷机,机长二三十米,每天24小时不停运转,工人三班倒。我们这一班有领班师傅、大师兄和我。师傅是劳动能手,还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做过公开讲座。大师兄也已出师,只有我是学徒工。每隔一周我们都有一天停机拆开大洗,然后再组装试车,这是技术要求最高的活儿。
上班半年之后,师傅教我拆卸擦洗机器的关键部分,然后组装起来,挺有意思的。后来有一天大修日,师傅让我清洗机器的核心部位,然后师傅和师兄就没影儿了。我只好自己完成清洗并组装好,再试车。等我全部搞完了,师傅就出现了。原来他是计划好了的,名师出高徒,从此他可以得意地在交接班会上说他的徒弟已经能独当一面了。
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消息不胫而走,10月21日报纸正式宣布了这个消息,终于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考大学了。报考是肯定的,但上学时学的并不扎实,又荒废了三年,而且时间这么短,怎么复习呢?
我们车间的支部书记是个复员军人,人很好,他给车间里的报考青工找来了政治复习题,这是在想方设法帮我们。同事、同学之间也分享找来的各种复习题,讨论习题答案。家里还有几本旧教科书,又在新华书店买了几本,复习就这样加班加点地开始了。我把公式抄在小纸条上,准备上班有空时好拿出来看上两眼。
可惜师傅太器重我,把我报考大学看成是不安心工作,希望我留下来。每当我从工作服兜里掏出公式要看一看时,他马上就支使我去干这干那。到最后干脆不和我讲话了。时间少得可怜,我也顾不得跟他解释。当时我们厂正在印毛选第五卷,提倡主动加班加点,我也不能例外,时间就显得更加宝贵。后来才知当年我们印“毛选”的纸张曾被紧急调用去印了高考试卷。
1977年高考是共和国唯一一次冬季高考。我和文革以来全国12届毕业生中的570万考生一起走进了考场,跨上了这座改变我们人生命运的独木桥。
北京的高考在12月10日和12月11日分两天举行,第一天上午考政治,下午考物理化学;第二天上午考数学,下午考语文。我的考场在车公庄的一所中学里,在那里还碰上了我的一位高中同学,他的一只眼睛长了一个硕大的麦粒肿,我都不好意思和他打招呼,看样子他复习得挺玩命的。我倒还好,复习时间这么短,谁都一样,着急也不管用。
第一天考完回家和哥哥按记忆对答案,有对有错。暂时放下考过的科目,集中精力考下一门。最后一门语文是命题作文“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正好我曾押过类似的题目,这是语文命题作文常出的题目。我在加班印毛选时想过这题目,所以开篇时比较顺,但后来也没写完。尽管如此,我的1977年高考还是在紧张,不安与遗憾中完成了。
考完试,刚松了一口气,马上又被忐忑不安的情绪包围了。“文革”开始后,高考已经中断了十年,这一次共有12届毕业生一起走进考场,竞争那么激烈,我能考取吗?天天企盼邮递员能给我带来喜讯。终于,有我的公函了!慌忙打开,还真是盼望已久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天,真是个好日子,阳光格外灿烂!
跨过独木桥,我和哥哥双双考上了大学,和全国27万幸运儿一起重返校园,成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圆了自己的大学梦。
从此,我们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
作者:黄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