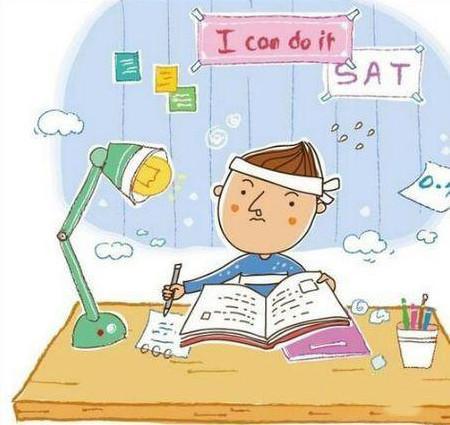过了几天,我在房里抽烟,在想去北京办理签证的事情,突然有人重重地拍我的门,并喊我的名字。我打开门见是系办公室的人。他手里拿着一张纸来到了我的房间,坐下后便把它递给了我。我一看便说这玩意我见过,不过已经被我扔到厕所里去了。他装得很大度,说他很为难。他一方面很同情我的处境,另一方面也不能违背系领导的旨意。他也抽起烟来和我闲聊。他说他也参加了系里的办公会议,其实只有系主任一个人主张我下乡,但其它人都不好反对。
系里把我的名单报到了学校之后,这就不再是一个系里的事情,而是学校的事情了。如果我不去的话,那么我就是违背了学校的政策。我问系里有十几名青年教师,为什么非要我去呢?他笑着说了一大串话,如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等等。他说我之所以倒霉的原因有三。其一,我的专业太突出了。如果我是一个默默无闻者,那么谁也不会理睬我。其二,我没有后台,没有一个大老替我说话。其三,我办理出国之事引起一些人的不快。他们认为我出国到天堂去了,因此去天堂之前吃一点苦头是应该的。
说白了,他们害怕我现在去了德国就不会到农村去接受一年的惩罚。如果我长期生活在国外,那么我将永远与中国的边远落后地区绝缘。如果我几年后回国,那么下乡的政策也许会终止。这是他们肚子里非常明白的事情。因此他们必须要在我办理护照尚未拿到签证时逼我下乡。这样不管我将来是否出国,我也吃了至少一年的苦头。此外这还隐藏着一种可能性:下乡一年的时间很有可能使我错过出国的机会。
这位办公室的人说,虽然大家都知道系主任是这么想的,但他却从来没有公开的说过。他决定安排我下乡是合乎学校政策的,已得到了系办公室的同意,且送到了学校。这就使问题变得复杂了。这位办公室的人对我有些了解,也知道我和当时校一级的个别负责人有良好关系。于是他建议我不妨去找一找人。但我说我办护照时已经麻烦过人家了,这次也就免了。我还笑着说我出国主意已定,下乡坚决不去,大不了辞职算了。那位办公室的人笑着与我告辞,说出国后不要忘了他。
办公室的人大概将和我谈话的结果告诉了系负责人。系负责人见他手下的人不行,便决定亲自出马来打击我的威风。一天我正在房里和两位朋友聊天,他们非常同情我的困境,但同时也给我打气,说我一定能如愿以偿,会尽快到德国去的。大家都在抽烟,房内烟雾腾腾,因此我把房门打开了。正在兴头上门口突然冒出了哲学系负责人的身影。他满脸愤怒的脸充满了杀气,仿佛是一副魔鬼之脸。他傲慢地没和任何人打招呼,便闯了进来。那两位好友见势不妙便出去了。
系负责人开门见山毫不客气地质问我:我为什么两次都不下乡。我说我办好了护照正准备去北京签证,而且可能就是下个月就去。他问我为什么不能先下完乡再出国。我说一年后所有的申报材料都将作废。他说可以再做,我说不行。于是他便火了,大声地斥责我,还使用了伤害和污辱我的语言。
这一下可激怒了我。我怒吼般地质问他为什么要打压我,不给我职称和其它东西,为什么不准我出国。他作了一些狡辩,但我毫不客气地将他赶走了。从此以后,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系办公室里,我都不理睬他,如同遇到一个魔鬼一样。我为武汉大学哲学系有这么一位不学无术且对人充满恶意的负责人而感到羞耻。
这位系负责人带着对我更大的仇恨走了之后,我想这件事也就如此算了。但过了不久我在房内又被急切的敲门声惊动了,原来是教师工作处的一位副处长和学校的一位专管青年教师下乡的负责人。看来我拒绝下乡的行动已形成了一个全校性的事件,惊动了学校负责人。但这两位学校的干部的态度倒是非常和霭可亲,他们似乎不是来对我采用高压政策威胁我,而是来说服我和劝导我的。见到他们这样的神情,我敌对的情绪便舒缓多了。我们一起抽起了他们带来的高档的香烟。
他们说明天学校就要开今年的下乡青年教师的大会了,我最好也能去参加。他们还说学校考虑到偏远地区经常停水停电,专门为每位下乡的青年教师买好了水桶和手电筒,我今天就可以去领。听到这里,我就打断了他们的话,说我今天不会去领什么水桶和手电筒,明天也不会去参加什么欢送大会。他们一听我的话脸便沉了下来,不过表现得还是非常有教养和策略。他们试图对我实施思想工作,其中一位讲他过去在工作上是如何不顺心,但忍一忍也就过来了,现在不是很好吗。
我对这种话没有任何兴趣,而是把我不下乡的理由重复了一遍。他们说学校的政策是不可改变的,但我也强调我的决心也是不可改变的。最后我和他们的态度和语气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知道说服不了我,便仍下了一句话,说校长已经知道了我的事,让我看着办吧。我说我大不了离开学校。
我拒绝下乡的事情传遍了学校,赞成和反对我的声音都有。我不管这些,仍然天天去系办公室,查看我的信箱里有没有重要信件。一天我碰到了另外一位系负责人。他居然毫不知趣地又要我下乡,我一听就火了,肺都要气炸了,和他拍起桌子来。我究竟见到什么鬼了,为什么这些人成天无所事事就知道逼我下乡?我嗓门很大,大声地斥责这帮打压我的人。也许因为我的声音如同雷鸣一般,所以大楼里的许多办公人员都跑了过来。
大部分的人是在看热闹,但也有人解围,仿佛是仲裁者一样,还有个别拍马屁的人装出了随时为系负责人护驾的姿态。不管这些,我大声宣布我决不下乡,任何人都无法动摇我的决心。也许是我这个口头宣言发挥了效力,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人胆敢和我提起下乡的事情。虽然我在哲学系没有后台,但人们通过这件事也知道了我,我是一个血性的汉子,不是那种甘愿做奴隶的人,而是一个敢于反抗自己命运的奴隶。
既然校方和系里不再逼我下乡,我也就不再主动提出辞职的事情。但我在系里却成为了一个异乡人,虽然他们仍没有能最终将我放逐到偏远的农村去,但还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将我放逐到哲学系一个孤立的角落去,除了每月领工资算是和系里保持一种关系之外,我和他们没有了其它的任何关联。一年一度的晋升职称评奖申请基金都没有我的份。系的负责人也许认为这也是对我的一种惩罚性措施。我也这么认为。但我不在乎,我真的是要走了。我还计较这些东西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