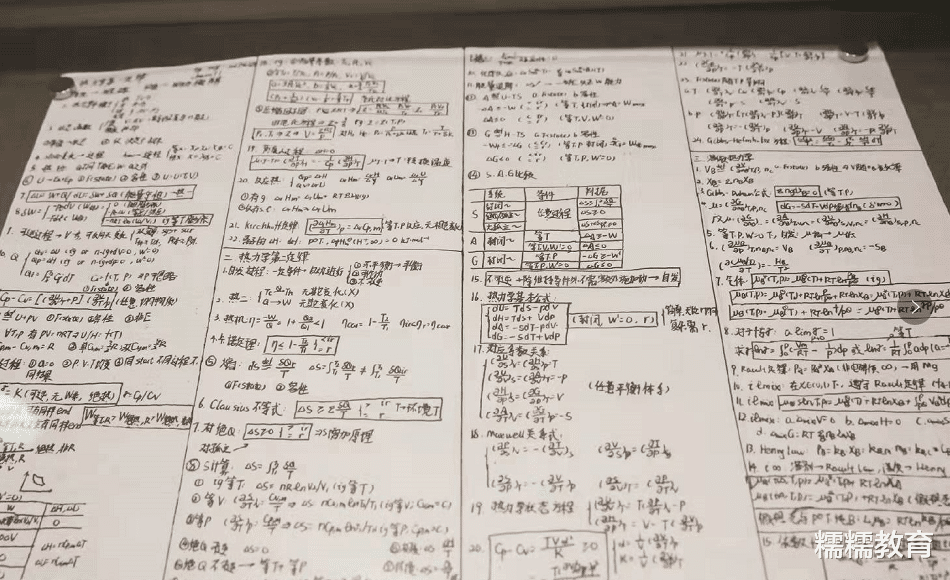美国教育资金继续向那些获得了更多科研经费以及收取间接费用比例最高的大学集中。1958年以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加利福尼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为首的前20名高校,获取的联邦经费占联邦资助经费总数的61%,而10年前的这一比例仅为32%。
而对于其他大学,尤其是具有一定研究能力的公立大学,联邦经费资助分布更广。截至1968年,40所大学中,每所大学收到至少1000万美元的资助,占联邦研究基金年度总金额的一半。这样做只能减小差距,却无法消除差距。加州理工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获取的联邦资助经费仍占其资助总金额的1/4强。优秀的研究中心也是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的,它们并不是仅仅依靠联邦经费资助发展起来的。
它们培养出的科学哲学博士一般在研究型大学谋得职位,因此减少了规模较小大学的人才数量。虽然科学研究领域的师生比例没有提高,但对教师和学生的资助完全不同。“联邦科研项目所造成的最不幸的后果就是导致了自然科学教师和人文科学教师地位和报酬的巨大差异”。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联邦资助经费减少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难道科学研究必须完全依赖一种资金来源吗?同其他高等教育经费开支相比,在1945-1975年间研究经费支出占大学经常性支出的8%。
尽管联邦政府提供了大部分研究经费,大学还是通过其他途径募集资金,包括大学获得的捐赠资金、州政府和当地政府的资助经费、企业赞助的经费以及基金会所提的经费。虽然也制定了其他的联邦计划,但未能实施。20世纪70年代初,人们讨论建立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基金会,但遭到声望较高的研究型大学的反对,因为基金会的建立将使联邦资助科学研究和研究生教育的经费分散到其他各个大学。这个例子说明高等教育的联合统一是如此之难。不同利益群体矛盾重重。
精英大学希望将联邦资金用于科研,社区学院希望将资金用于资助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州立大学则希望将资金分配至更多的大学。国家教育研究院建立的初衷是支持并资助研究教学、学习、学生入学和学生资助等方面的问题,但在几年后因领导不力和缺乏高等教育团体的支持而垮掉,后来又相继建立了联邦教育研究与发展办公室。因为对联邦政府的不信任,加之精英私立院校为了保持其优势地位以及院校的独立性,保护院校自治的呼声不断高涨。
参议员丹尼尔·莫伊尼汉评论说,“最初建立高等教育主要源于历任总统及其政府的政治利益和政治目标,虽然要求高等教育实行这一目的,然而高等教育很少遵照执行”。高等教育机构和联邦政府之间的关系就像是两头互相对视的小心翼翼的巨兽。双方不断努力,试图解除对方的猜疑。联邦政府在《国防教育法》中要求获得联邦资助的院校进行忠诚宜暂,遭到众多院校的反对。学生要求取缔大学的后备役军官训练团,并撤出军队征兵人员,以示对立法者的抗议。
尽管如此,联邦政府和高等教育仍互相依赖。学生资助仍是联邦拨款的一大特色,科研资金通过众多渠道,不断输入高校。联邦政府采取向低收入和其他困难学生提供资助等多方面的措施,拓宽了资助范围,并允许高校增加学费。令人惊奇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未经过高等教育机构政治上的专门努力。这一方面是因为高等教育得到了组织良好的中小学教育联合会的帮助;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国会和政府为了满足更多的公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
到这一时代末期,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的理事会对联邦资助提出建议,指出由于高等教育成本飙升,必须增加联邦资助经费。高等教育委员会建议采取多种资助方式,其中包括:直接资助大学;资助大学建设以容纳不断增多的大学生;提高研究经费;实行国家学生贷款,以保证所有的学生能够接受高教育,同时允许学生毕业后低息偿还贷款。委员会建议增加1972年批准推行的基本教育机会助学金,并呼吁全额资助这项计划以及大学的学习效率研究计划。
联邦应加大对职业教育、图书馆和研究生奖学金的支持力度。委员会承认联邦政府对上述所有领域的资金支持都有所增加,但同时指出,由于通货膨胀的增长速度更快,联邦政府的实际资助额出现缩水。虽然委员会并未直接向华盛顿联邦政府提出建议,但其出版各种书籍和发行物等产生的间接影响可谓巨大。联邦政府对研究生奖学金的
资助在1967年以后的十年间减少60%,对本科生的资助却飞速增长。联邦政府转向资助提高大学入学率的趋势日益增强。
慈善捐赠这一时期的慈善捐赠增长了10倍,校友和其他个人、公司、基金会以及宗教组织的捐赠均有所增加。个人所得税税率的调整刺激了高收入人群的捐赠积极性,比如规定:每个捐赠者捐赠100美元就可以冲抵30美元的个人所得税。以私立大学为首的大学做了大量的募捐活动。1957年哈佛大学的募捐活动获得了高达8200万美元的捐赠,而此后不久,斯坦福大学开展的一场募捐活动获得了1亿美元的捐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企业捐赠。
1935年修订后的联邦税法允许公司最多扣除5%的税前净收益,用于慈善捐赠,促进了捐赠的增加。尽管如此,企业捐赠仅在1945年才超过其税前收益的1%,原因是对企业捐赠是否需要获取股东批准这一问题长时间难以得出答案。关于该问题,有一个典型案例:1951年史密斯公司向普林斯顿大学捐赠1500美元,股东对此向新泽西州最高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对此次捐赠予以认可,并允许公司无需获得股东的预先批准,即可进行捐赠。
其他公司展开了形式多样的资助活动:福特汽车公司宣布为员工子女提供奖学金;1955年通用电气公司也发起了一项配套捐赠计划,公司将根据员工捐赠数量提供相应数量的捐赠。1975年,公司捐赠约占捐赠总额的1/6。慈善基金会继续为高等教育提供资助。联邦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征收高收入所得税,并于朝鲜战争期间再次征收,许多公司为了避税纷纷建立基金会。这期间,基金会总数是战前的5倍,部分规模较大的基金会向高等教育提供了大量慷慨资助。
1950年以后,福特基金会的捐赠超过了20本世纪初期极具影响力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1953年,福特基金会的捐赠占基金会捐赠总额的1/3。三年后,福特基金会捐给私立学院和大学的总额超过2亿美元。这些资金用于教员加薪,颇受各院校欢迎,尤其是教员工资水平较低的小型私立院校。福特基金会还通过提供资助的方式,鼓励私立院校提供配套资金,以促进他们所希望研究领域的研究。慈善基金会一般会大量资助医学研究和大学研究。
同时还资助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由于联邦政府忽视这方面的研究,因此相对比较落后。卡内基基金会为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以及其他大学的各种国际性研究工作提供资助。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下,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俄罗斯研究学会,用于培训政府工作方面的专家。福特基金会资助社会科学研究,其资助的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在该领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芝加哥大学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也获得了资助。
结语
在1949-1950年和1975-1976年间,各种渠道的慈善捐赠比例保持稳定,除了公司捐赠由12%增长至16%。但是,由于政府资助增加,高等教育总体捐赠中慈善捐赠在大学收入中所占比例由这一时期之初的9%左右滑落至最终的6%,而大学来自捐助、销售和服务、附属企业和医院的收入也出现下滑,州政府及地方政府资助不断增长,超过资助总额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