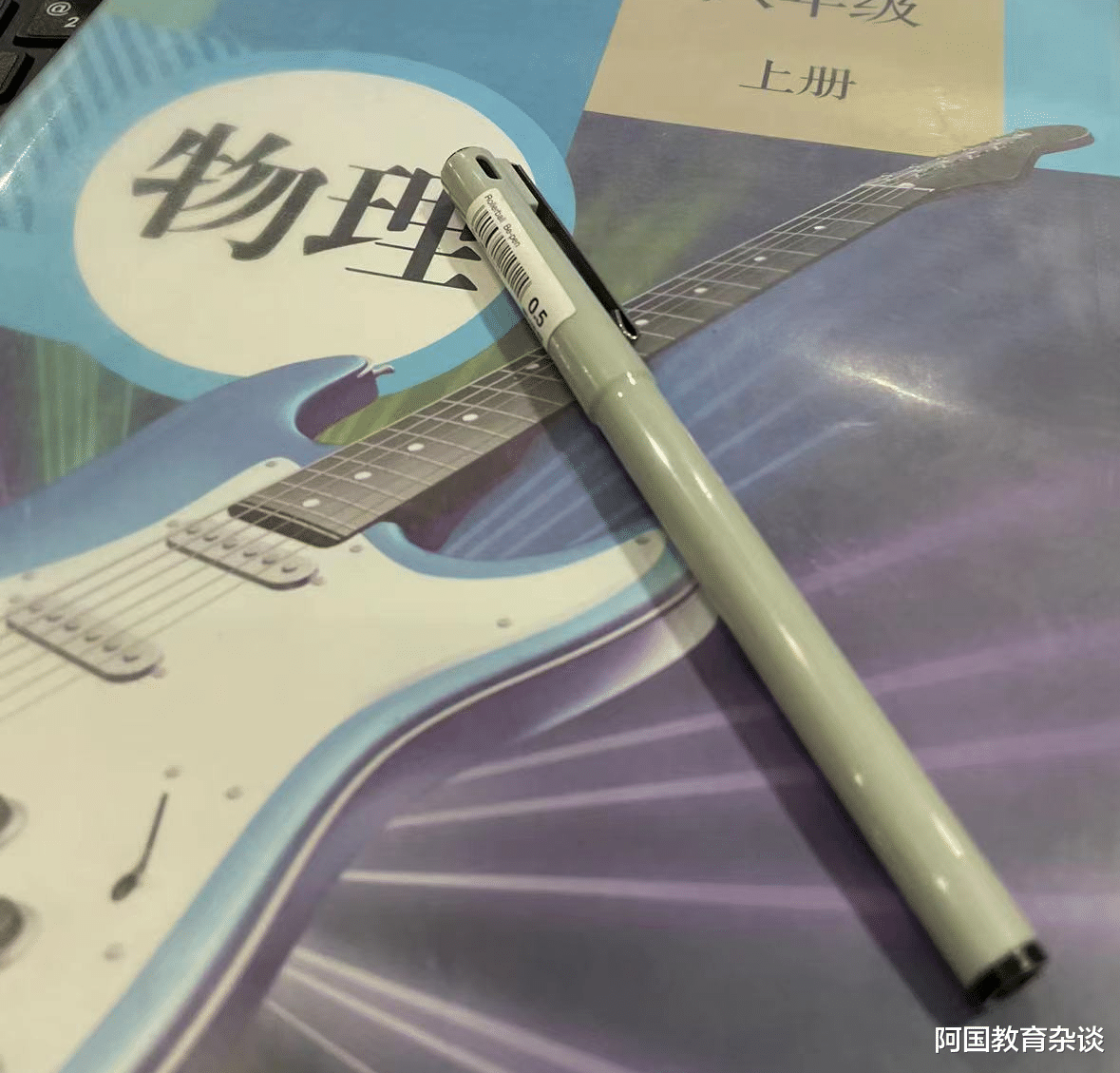我在复旦大学执教四十年(1982-2022),期间担任过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2006-2012),这使我有更多机会造访国内几乎所有著名的高校。每每我第一次去该校访问,好客的主人总会派人陪我游览他们的校园。北京大学的未名湖,武汉大学的樱花,中山大学的珠江河畔,厦门大学的海滩……各大学的著名景点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游览完毕,陪我的老师总会顺便问一句:“复旦大学也很美吗?”这话充满着对自己学校美景的自豪。
我也会自豪地回答:“复旦大学当然很美。”
“那最美的景点是什么?”
“课堂!”
“啊,什么地方?”
我提高声音,拉长声调再说一遍:“课堂!
左图:青年时代的李良荣老师;右图:2012年,李良荣老师在学术交流时发言。作者供图我读过徐志摩写的《我所知道的康桥》,以诗人的笔触把剑桥大学写得美轮美奂。但无论是徐志摩笔下的剑桥大学,还是国内著名学府的景点,都只是自然美景、建筑景观,复旦的课堂才是我心中最美的风景。
复旦大学邯郸路大学本部共有6幢公共教学楼,我都听过课、讲过课。而最难以忘怀的是一教和三教,它对我的人生转折具有标志性意义。
我1963年考入新闻系,秋季入学第一堂课是在一教的101室。一教,老复旦人都称为“老教学楼”,是在复旦大学创办时就建立起来的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这第一堂课由历史系一名老师上党史课。这课让我很新奇,倒不是有什么新知识点,而是老师提出问题让我们讨论,鼓励同学发表不同观点并展开争论。她也不评判谁对谁错,而是开出几篇文章让我们课后去阅读。我感到很新奇:大学的课原来是这么上的!这堂课开启了我5年的大学生涯,也让我对大学生活充满憧憬。但我的憧憬很快破灭。5年大学,只上了1年课,其间还有3个月报社实习,几乎没有听到多少课。
11年后的1979年秋,我考上研究生,再次进入复旦大学,而我的研究生生涯却是从笑话中开始的。入学第一堂课是英语,在一教102室,由外文系张增健老师执教。张老师黑黑瘦瘦,中上个子,一开口就自我介绍是外语系66级的(即1966年毕业):“我的年龄和在座许多人差不多,台上是师生,台下是朋友。”很亲切,一下子拉近了关系。接下来,张老师让我们打开课本,要求同学每人读一小段。大家都读得很流畅,张老师不断点赞“好”。最后一个轮到我读,我有点尴尬地对老师说:“英文字母都认识,但不会读,读不出来。”他瞪大眼睛问:“怎么不会读?”我回答:“我高中、大学都学的是俄语,英语自学8个月参加研究生考试,勉强及格。”张老师似笑非笑:“自学8个月,考研究生过关,厉害。我要听听自学8个月的英语水平。”我只好说:“老师的话必须听,我读,只是请老师别笑我。”
于是,我开始读,还没有读到一半,全班同学都笑翻了。我结结巴巴,一个词一个词地蹦出来,无法连贯读,还读错了。张老师回到讲台,一声咳嗽,全班安静,他笑眯眯地看着我,缓缓地说:“我教了10来年英语,你读的是哪门子外语?”再次把大家笑翻。我假装生气,回怼他:“张老师,我们约定,你不能笑话我。现在你这么讥笑我,打击了我学习积极性。”张老师笑起来了,说:“抗议有理。”下课后,走出课堂,张老师把我叫住,居然递根烟给我:“有空多读读,不清楚随时问。”从此,张老师再也不曾为难过我。
一学年,张老师每星期给我们上两次课,每堂课,除了讲课本上文章,还穿插英美等国的故事、各类笑话,兴致来时还会背诵雪莱的诗、莎士比亚的名句,时不时拿学生的作业错误开涮,课堂里总是笑声不断。他全英文讲课,我似懂非懂,课后借同学的笔记才能基本搞懂。张增健,一位有趣的老师。
过后几年,我和张老师成了好朋友,去过他家几次,满屋的书柜,书柜里满是英文原版书、各类词典,张老师太太半埋怨、半赞扬:“一大半工资都在书上了,不靠我工资,家里喝西北风。”我这才明白,张老师平平常常的一节课,确是多年的积累。
一教更让我难忘的是我陪着我的导师王中老师给新闻系77届学生上课。王中老师上课,没有任何讲稿,语调不紧不慢,娓娓道来。有些话,学生听不清,我写在黑板上;有些引文,他记不清,我补充几句。记得王中老师最后一次给77届学生上课是1981年春末。
在上课快结束时,他问我:“昨天郑北渭老师来,讲到报纸的功能时,他怎么说的?”我回答:“郑老师说,美国新闻界有句流行语说,报纸是国家的看门狗。”“对,就是这句。”他转身对学生们说了最后一段话:“国家看门狗,要保护国家利益,保护人民利益。做一只看门狗,要看清真实情况才报警,不能一犬吠影,百犬吠声,捕风捉影,人云亦云。当记者,必须向人民报告真实情况,有些事不能公开说,可以沉默,但绝不能说假话,报道虚假新闻,误导公众。这是我最后一堂课,留给你们最后的话。”
当时,整个教室鸦雀无声,我看到许多同学眼含眼泪。过了一、二分钟,掌声响起,然后全体同学起立。在阵阵掌声中,王中老师缓缓起身,向同学们挥一下手,在两名学生搀扶下走出教室,走出一教,我陪他回家。但走了一段路,王中老师又转过身凝视了一教,似乎自言自语,似乎又在告诫我:“青年还应该有新闻理想的。”“新闻理想”,这是我终身难忘的一个词。
如果说我的两次学生生涯从一教开始,那么我的教学生涯是从三教开始。1982年秋,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到1983年秋,我正式登上讲台,接过王中老师的教鞭,给新一届学生上《新闻学概论》。过去了四十年,这一堂课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宛如昨天。那不仅仅是因为这堂课正式开启我的教学生涯,而是走进教室的那一瞬间。
尽管我为上好这第一课做了种种准备,预设了许多可能发生的状况,但当上课铃声响起,我踏进三教202室,刚刚还窸窸窣窣的低语声,一下子静下来,教室鸦雀无声,同学们齐刷刷抬起头望着我走上讲台。我向台下巡视,同学们都仰着头,睁着明亮亮的眼睛,那是青春灵动的眼光,那是渴望求知的眼光。我不知是慌乱还是激动,脑子一片空白,想好的开场白全忘了,只好实话实说:“这是我当教师的第一堂课,也是你们进入大学的第一堂专业课,对我,对大家,都是难忘的。”突然间,掌声响起。这掌声给了我勇气,我放开胆开始讲课,伴随着下课铃声,同学们再次给我掌声,这是我渴望得到的。留校任教并非我的本意,因为我理论功底差,外语水平低,一口宁波国语,很没自信。是学生的鼓励,给了我当名好老师的自信。
“齐刷刷抬起头,闪动着渴望求知的眼光。”这成了习惯性的场景。这样的场景仍然一次次使我感动,激励我当名好老师,不要让学生失望。我知道面对我的学生都是全国学习尖子,未来将成为各媒体的骨干、顶梁柱,甚至领军人物,支撑中国新闻界的未来。
那时,我喜欢听刘兰芳说书,她说的杨门女将故事家喻户晓,但我还是喜欢听刘兰芳绘声绘色、激情四射的戏说。有一天突发奇想,如果上课也像刘兰芳那样,不更吸引学生吗?自此以后,我听刘兰芳说书不仅仅是业余享受,更是一种学习、模仿。渐渐地,我享受上课,踏进教室,面对学生,我什么烦恼都没有了,什么病痛都消失了,只有全身心的投入。学生们喜欢听我的课,甚至称之为“阳光灿烂的日子。”
每学期教学评估,我长期是学生评分第一名。从教40年,我获奖无数。最近一次奖是2021年,我写的《新闻学概论》(第六版)获得教育部全国教材建设奖二等奖,同时获得首届复旦大学教材建设特等奖、首届复旦大学教材建设特别贡献奖。但我最看重的却是2007年我同时获得“我心目中的好老师”“我心目中的好导师”的称号,这是复旦大学第一次由本科生、研究生海选出来的。
我对来上课的学生是很放纵的。开学第一课我就告诉学生:“我的课是必修课,但我不会点名,只有两个要求:不要迟到,不要发出噪音,不影响要听课的同学。如果有事不能来上课,不必向我请假。如果我课上得不好,你们不喜欢,可以不来;来了可以不听,大大方方看其他书,写诗写情书都可以,只要期末参加考试。”但我基本没有发现无故不来上课的学生,也极少发现在课堂上做其他事的学生。
我明白,我尊重学生,学生们同样给我足够的尊重。给研究生上课时(教室在新闻学院教学楼),看到学生为了不迟到,都一路飞奔而来,很多学生肯定来不及吃早饭,一个上午往往四节课要饿肚子,对学生身体极其不利。为此,我向全班同学宣布:“允许你们上课带早餐来课堂吃,但不许出声,掉在桌面上、地上的渣渣,都必须收拾干净,能做到吗?”全体学生拍着桌子都喊:“能!”
自此,课堂上,半数左右学生尤其女学生都是边吃早餐边听课,奶香、葱香、饼香,满教室飘香。有一次,一名女学生把脆饼咬得嘎嘣响,我停下课,责问她:“你知罪吗?”那名女生战战兢兢站起来:“我发了声响,犯了规。”我数落她:“你咬得嘎嘣响,很爽,有些同学没吃早饭,我听到他们肚子咕咕叫了。”引起一阵哄笑。
在三教,有一间在全国高校闻名的教室:3108室。3108室并不大,可以容纳一百来号人,没有特别装潢,和三教其他教室一样。不知从何时开始,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新世纪前10年,长达20年的时间里,都是复旦大学具有标志性的学术殿堂。
那时老复旦人都流行一个说法:在相辉堂演讲是最高的政治礼仪,在3108室演讲是最高的学术敬意。国内一批知名学者一听说安排在3108室演讲,都会诚惶诚恐,一再表示感谢。那时候,学校大门口的布告栏贴满了各场演讲广告,有一次,我数了一下,那天的演讲多达12场,中国与外国的,历史与现实的,文科理科,各类题材都在布告栏里交汇,荣誉加身的年长学者和初出茅庐的博士生、著名的企业家、各级政府官员、声誉全国的艺术家,都同时在布告栏上亮相。
复旦大学作为全国著名学府,请人来演讲不难,但吸引学生来听演讲却很难。如果偌大一个教室只有十几位听众,主办者有多尴尬?所以,老师们都会把自己的研究生叫去听课撑场面。但3108室的演讲,听众都是里三层外三层,主持老师都会让研究生早点去会场维持秩序。2001年春,一位来自北京名校的教授在3108室讲“世界文明的进程”。7点钟开讲,我6:30左右赶到现场,发现教室里早已挤满了人,教室外的窗口都站满了。我挤不过学生,只好回家。
我在3108室听过的一次课是历史系姜义华老师讲“中国现代化之路”,姜老师是我的师长,他从中国历史的维度来研究中国现代化,我十分敬重。那天,7:00开讲,我6:15到3108室,总算在后排找到一个座位。很多学生面前都摊开电脑或笔记本,但坐在我右边的几名学生什么都没带。我有些好奇问他们是什么系的?身旁的那名学生指着旁边几名同学回答我:“我们几个都是化学系的。”我更好奇:“你们理科生怎么对文科感兴趣?”那名学生又答:“我们都一个宿舍的,在这里听过很多次课,回去还讨论到深更半夜。”姜老师讲课到9点,提问环节,齐刷刷举起手来,问答到10点,主持人不得不宣布结束。课上完了,一大批人还把姜老师围在讲台上问个不休。
很幸运,我应邀在3108室讲过一次课,那是2007年期末,讲的是中国传媒业改革。现场人山人海,连讲台的四周都坐满人。那次演讲,我的一句话曾在复旦很轰动:“年轻人,少谈政治,多谈恋爱。”这话是学生提问时我随口蹦出来的。正式演讲结束后,到提问环节,一名学生大声问我:“李老师,有一个问题在我们班级中争论很久:大学生该不该关心政治?”这个问题可能切中要害,全场肃静,听我怎么回答。对于这样的敏感话题,我可以搪塞过去,但我的性格是不回避学生的任何尖锐问题。
我这样回答:“这不是yesorno的问题。我认为,不同学科会有不同要求,比如我们新闻传播学专业,将来去当记者,不关心政治,会犯政治错误;而其他学科尤其理工科学生,对关心政治的要求没有这么高。不同历史时期会有不同要求,当国家在存亡之秋,大学生当然应该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命运。现在我们国家政治清明,政通人和,你们只需要了解一下国家大事就够了,要那么关心政治干什么?《在希望的田野上》唱的是老年人举杯,孩子们欢笑,小伙儿弹琴,姑娘唱歌。那歌里没有中年人,中年人就是干事业的,政治就是中年人的事。对大多数大学生来说,把书读好,把自己事做好,将来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报效祖国。有时间有精力就多去谈谈恋爱。年轻朋友们,少谈政治,多谈恋爱。”想不到,全场起立,长时间鼓掌。“少谈政治,多谈恋爱。”一时传遍复旦校园。听说,有人告到校领导那里,有名副校长为我辩护:“大学生谈什么政治?空谈误国。”
复旦的课堂,白天学生们在课堂进进出出,像人潮,潮涨潮落。到了夜晚,整个教学楼都灯火通明,教室里座无虚席,同学们都在埋头看书、做作业、做笔记,一、二百号人的教室几乎都鸦雀无声。望着整个教学楼通明的灯火,看着同学如饥似渴地学习,我总会由衷地感叹:世界上还有比这更美的风景吗?
这就是复旦的课堂。教师们在课堂上挥洒着汗水和热情,寄托他们的理想和追求,无论是个性张扬、神采飞扬的演讲,还是细声慢语、娓娓道来的讲解,平平常常一堂课,都是教师们精心准备,把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研究积累传输给学生。“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教师就是课堂上的源头活水,把知识,把智慧像泉水一样源源不断注入学生脑海。一代又一代的教师,薪火相传,在课堂上奉献青春,度过中年,慢慢老去,无怨无悔。
这就是复旦的课堂。古今中外的知识,人文社科、理工医科的知识,在课堂上交融,各种观念、观点,各种思想、思潮,在课堂上交流、交锋,扩展学生的视野,启迪学生的思考,理清学生的思路,引导学生去探索。复旦大学的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就在课堂上实践。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复旦的课堂铸就复旦人的品格:自由而无用的灵魂。
课堂,复旦最美的风景。
我永远眷恋着复旦的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