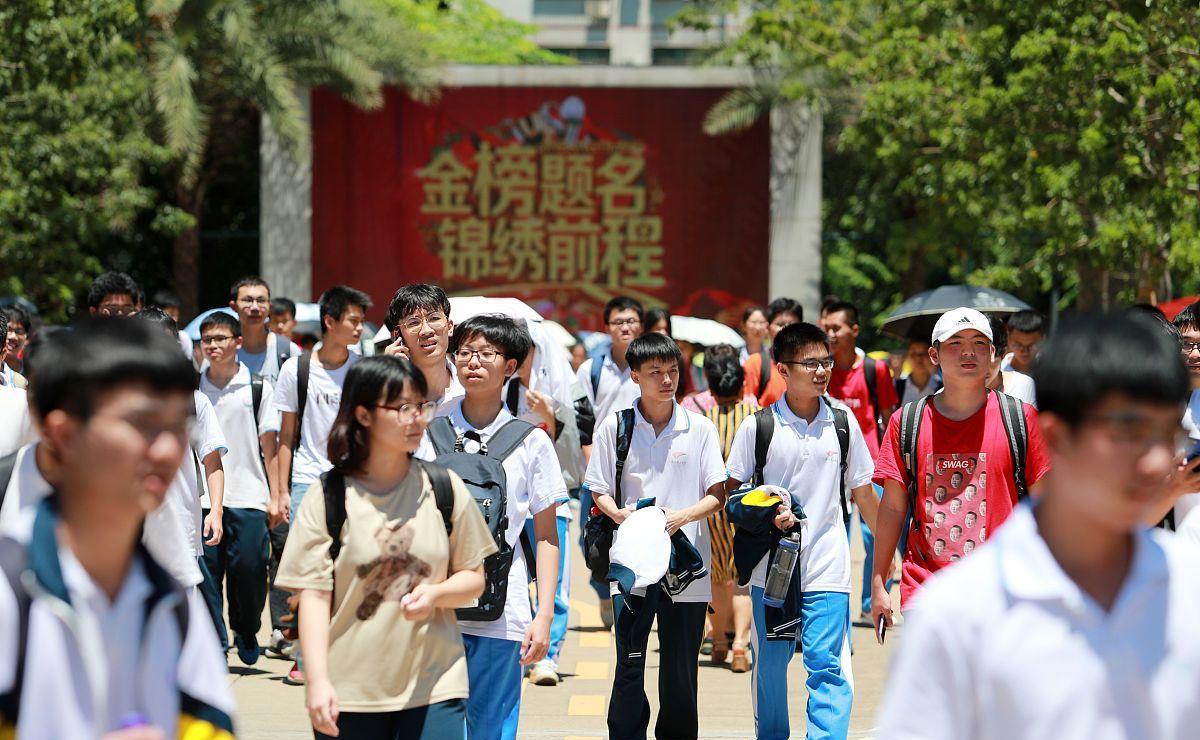罗翔是网红司考老师,也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他经常依据法学、法律的逻辑,对中国的一些社会现象提出批评。近日,他又为犯罪子女被禁止报考公务员喊冤,认为这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
司考就是司法考试,是法律从业者的资格考试,罗翔也兼职从事司考培训,并因激情而风趣的讲课风格而成名。
为论证不应该禁止犯罪子女考公的观点,罗翔写了一篇四五千字的长文(《一人犯罪影响子女亲属考公,这公平合理吗》)。但通篇读下来,其所引用的历史、知识和逻辑,全部是西方的,没有半点中国的东西,然后就开始下结论了。作为一个学者,论述中国的公务员考试问题,却丝毫可以不考虑中国的历史、文化和逻辑,然后就大胆做出论断,丝毫不用担心其观点的无知者无畏,请问谁给了他如此大的胆量和勇气?
其实,这种在学术研究上脱中入西、入主出奴的现象,在当今中国学术界是非常普遍的。记得多年前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一场关于儒家哲学的研讨会上,有一位教授发言称,自己是研究西方哲学的,对儒家经典不太熟悉,然后又说,他认为儒家如何如何。
既然连儒家经典都没有读过,又有何资格对儒家评论。更令人惊诧的,这位堂堂的大学教授,丝毫不以自己没有读过儒家经典有何不妥,更不会以为羞耻,而是仍然认为自己完全有资格对儒家评头论足,他的自信就来自他所读过的西方哲学,以及因此所获得的学位证和教授资格。
也就是说,在他们眼中,在基于西学的博士学位和教授资格面前,中国的传统经典、传统知识无足轻重,无关紧要。他们潜意识认为,西学绝对地凌驾于中学之上,西方文化也绝对凌驾于中国文化之上。或者说,压根没有中学,中学压根不是学,而只有西学,只有西学才是真正的学。
当前中国已经实现在硬实力上的崛起,已经摆脱了西方殖民统治,甚至可以直接向昔日的列强直接叫板、对抗,但是在学术领域,在学者身上,却依然是深陷殖民统治之中。更可悲的是,他们甘愿接受这种统治,甚至感觉不到统治的存在。
这种情况非常类似于强盛的大唐。现代人列举中国历史上的辉煌,首选就是所谓的“汉唐盛世”。其实,唐朝之强和当下中国之强一样,都是强一半,经济强、军事强,但学术和思想不强。当下中国的学术和思想深陷西方的殖民统治,唐朝的学术和思想则深陷佛教的殖民统治。
中国对佛教的传统认知,也是源自遥远的西方,也是西来的,属于当时的西学。唐僧取经也去的也是西天。
中唐时期的韩愈,也是历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不仅散文写的好,而且思想也很深刻,他对当时的中国在学术和思想上深陷佛教的统治而极为痛心,大声疾呼要改变这种局面。于是他就写了一篇《原道》,成为中国学术和思想史中的不朽丰碑。
顾名思义,“原道”就是追溯和辨析什么才是真正的“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知识和逻辑。韩愈认为,中国传统的儒家义理式的知识和逻辑,才是真知识和真逻辑,佛教、道家的知识和逻辑则是伪知识和伪逻辑。主张重回儒家,而排斥释老。
当然,这种脱西入中的,回向中国义理传统的学术和思想变革,直至两宋才真正实现,儒家义理之学,压倒佛教之禅理,成为中国主流、主导的知识和逻辑。
韩愈说:“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这句话后来被简化一个成语“入主出奴”。
意思是说,对于存在矛盾的两套思想体系,如果你选择相信一家,让它进入和占据你的头脑,你必然会以它为主人,依附于它,甘愿接受它的统治。相应地,你就会把另一家选择不相信,将其赶出你的头脑,然后以其为奴仆,对其进行谩骂侮辱。
在唐朝,中国的传统的义理思想,就不幸成为“出者”,被“奴之”、“污之”,佛教、道教则成为“入者”,被“主之”、“附之”。
当下的中国和韩愈时的唐朝一样,中国传统的义理思想,也成为“出者”,而西方外来的思想成为“入者”。只是唐朝时作为“入者”的西学是佛教,现在作为“入者”的西学则是科学。
其实之科学,和昔日之佛教,本质相同,都是无神的宗教。其弊端都在于,正如韩愈所指出的,脱离历史和实践,脱离实际和人心,而是以人为虚构的概念和理论为基石,将虚构的伪概念伪理论凌驾于历史、实践和人心之上。
佛教的虚构概念是“清净寂灭”,科学虚构的概念是“科学真理”、“客观规律”。佛教以“清净寂灭”最高真实,它凌驾于历史、实践、人心之上,甚至以真实的历史、实践、人心为虚幻。科学以科学真理为最高真实,认为历史、实践和人心都必须服从它。
也就是说佛教和科学的共性都是,以其虚构的概念为最崇高和真实,以真实的历史、实践和人心为低贱和虚幻。
很多人说,科学不是讲科学实验的嘛,它很重视实践的啊,也是以实践为基石的啊。没错,科学的确很重视实验室的实验,但是,科学真理的概念,并非自这些实验室式的实验中产生,而是在科学实验的概念产生之前早就存在。
实际上,科学真理是对基督教神学真理的继承,两者本质相同。而神学真理,则是上帝的属性,它是绝对地超越甚至否定真实的历史、实践和人心的。
也就是说,科学中对实践的重视,是有限的,这很像现代西方民主、自由、法治这些概念中,在实践中其真正的民主、自由、法治是有限度的,超越这个限度和阈值,是绝无民主、自由和法治的。在科学中,超越科学试验的限度,就绝无实践了,而是先验式的预设。
科学试验并非发现科学真理本身,而只是证明科学真理的存在。科学真理本身是凌驾于科学试验之上的。
而且科学试验和真实的实践又判若云泥。实际上将科学试验当实践本身就是一种虚构。真正的实践是存在于广阔的真实社会之中的,而科学试验却仅仅存在于与世隔绝的小小实验室之中。
其实,近日之与世隔绝的实验室,与昔日与世隔绝的宗教庙宇并无本质区别,两者也都认为自己可以在这个与世隔绝的狭小空间,可以发现和体验人间真理,与真理同在,然后拯救苍生。
真实的实践式的实验,应该以整个世界整个社会为实验室。
也就是说,脱离历史、实践和人心,是现代西方学术的固有属性,他们在思考和论证问题时,不是从真实的历史、实践和人心出发,而是从虚构的概念和理论出发。
所以,包括罗翔在内的当下学者,在论述当下中国的实际问题时,才可以肆无忌惮地无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逻辑,而奉西学中的虚构为真理,无知无畏,教条迷信,背离实际和民心。
这也是韩愈所痛斥的“入主出奴”历史现象的死灰复燃。
关于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逻辑出发,去论证禁止犯罪者子女考公是否合理,请关注本号的后续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