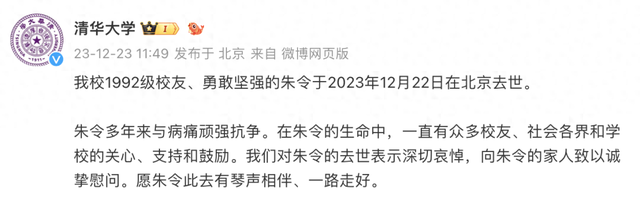记者曲鹏
2020年底,全国共有普通高中学校1.42万所,其中县、县级市举办的普通高中7243所,占比51%,县中在校生1468.6万人,占比59%,县中及其学生的数量均已占据半壁江山。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无论是高考升学率,还是办学质量,县中都曾涌现出一批成绩领先于大中城市高中的优秀学子,然而在近十年,县域教育却成为亟待振兴与帮扶的对象,越来越多非发达地区的县级中学风光不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最近出版的两本新书,《县中的孩子》和《县乡的孩子们》不约而同地将视线聚焦于县域教育现状。处于基层的县域教育,是中国教育的底色和普通教育赖以生存的基础,更值得我们关注,诚如《县中的孩子》作者林小英所说,“教育不该是适者生存的模式,经济越落后的地方,教育越应该给人以希望”。
林小英著
雅理·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杨华雷望红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批县域高中在高考升学率和办学质量上遥遥领先,改变了无数乡村学子的命运,甚至吸引了不少城市的孩子到县域高中就读。那时,“县中现象”令人瞩目,县中也成为诸多乡村学子改变命运、实现社会阶层跃升的主要渠道。
进入2000年,县中风光不再,由于条块分割的教育行政体制以及跨区域的生源市场的形成,越来越多非发达地区的县级中学日趋衰败,成为一个问题式的存在。
对大部分县中来说,普遍面临着这样的问题:生源之困、师资之困、硬件之困、保障之困、质量之困。具体表现就是,跨区域掐尖招生、优质师资外流、教育投入不足等,其结果是升学率降低、教育质量下滑。
《县乡的孩子们》指出,破坏县域教育完整性的外部因素有两个。一是民办学校的发展。在一些地方,小学毕业生想进好学校读书有两个途径,要么进民办初中,要么去外地找好的公立初中;再通过掐尖、初高中剥离等方式弱化公立优质高中;跨区域集团化办学的民办学校还掐尖县域生源,破坏县域高中生源结构和县中模式,从而弱化整个县域的基础教育体系。二是教育城镇化发展。“教育新城”“教育地产”模式,把大量的优质教育资源和公共财政资源集中到新城,打造明星学校、亮点教育工程,抽调走乡村优秀教师,人为打破了城乡教育质量均衡,拉大了城乡教育差距。
学校之间不断上演着“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生源和师资争抢,冲击了基础教育的生态,导致有的地方营养过剩,有的地方无人问津。人们都简单地将责任归咎于滞后的经济发展,很少有人认真思考什么才是回归本真的教育,“当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高考的时候,很多的问题会被掩盖”。
《县中的孩子》作者林小英将县中的孩子归结为贫富差别和城乡差别两个维度叠加构成的连续统一体中的一端,而这一端中的群体又可以再次被划分为“村小的孩子”和“县中的孩子”两个成长阶段,这两个成长阶段则分别对应了两次重大筛选。从“消失的村小”到“没落的县中”,县域的孩子们在不同跑道上起跑,面临着怎样的生存之困与学习之难?
书中把生活困难的学生总结为四类:家庭不健全、经济困难、路途遥远、长辈需照顾。这些孩子在拼尽全力进入高中后,面对升学压力、朋辈压力、社会差距和认知成长等因素,使得他们所承受的生存之困被加倍放大。某县中老师告诉林小英,他们学校的学生家庭情况特殊的特别多,有父母离婚的,有家庭重组的,或者父母没离婚,有一方突然离家出走的,孩子能够上学撑到现在已经很不易了,“越是乡镇和乡村的学校,由于家庭的特殊,给孩子们造成学习的困难就越大”。对这些孩子来说成绩都是次要的,“只要他能够坚强地生存下来,能够健康,这已经很不错了”。他们这些孩子中的很多人,会在县域接受自己生命中最后一个阶段的正式学校教育,他们对教育的需求、对学校的需求,不单是提供升学预备的知识,更是培育情感和培养技能。
尽管县中的孩子大部分时间并不处在农村,他们对自己并没有主动意识设计的生涯规划,医生、警察、教师、公务员是他们所能想到的最好、最稳定的工作,却无法预见到其他更精彩的生活类型。某县中一位高二文科班学生坦言自己并没有特别想做的事,觉得当老师是一个安稳的工作,“还可能回本县,毕竟在家这边,比较熟悉”。
县中教师对孩子们关于学科与未来就业的指导也十分有限,某县中一位理科重点班学生说,他的老师只是告诉他“理科容易找工作,选择的余地比较多”。
面对生活的艰辛,更多的家长让孩子在潜意识里降低了对未来的期待,安稳的生活就是人生理想。某县中一位高一学生家长告诉林小英,孩子能考到什么就是什么,考到哪里都支持。还有的家长宁愿让孩子考入本省的高校即可,“孩子还能回到本县工作,可以照顾一家人甚至一个家族的人,也可以得到家里更多的照顾”。
在调研中,林小英意识到,眼界的限制、资源的匮乏,使得县中的孩子在学业基础、学习习惯、学习投入、竞争意识、职业规划等方面确实处于弱势的地位。“这些县中的孩子,同样也是我们的孩子,他们终将会长大,融入社会的洪流之中,不论是富孩子还是穷孩子,超级中学的孩子还是县中的孩子,最终都是在某一个社群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退回来讲,必须承认,我们对县中的孩子负有照看的义务和责任,而不应该只是袖手旁观。”
公共教育是绝大部分农民家庭获取教育资源的唯一途径。随着农民家庭经济条件改善和教育预期提高,日渐衰败的乡村教育已经难以满足农民家庭的教育需求,为了让子女获得优质的教育机会,农民家庭不得不成为拼夺教育资源的竞争主体,并被裹挟到进城陪读的大潮中。
大量的乡村学生进入县城上学,对餐饮、住宿、公共交通等县域教育基本公共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但中西部大部分县城没有经济能力来满足这种需求,农民家庭不得不通过调整家庭分工来应对。打工经济兴起时,年轻人外出务工,早期的陪读主要是隔代陪读,奶奶在县城租房陪读,爷爷则留在村里种地或打零工,而近几年,返乡陪读的80后、90后年轻妈妈越来越多,成为陪读大军的主力。
《县乡的孩子们》作者在调研中发现,很多家长从小学阶段就开始陪读,初中、高中更是必陪阶段,而且不管孩子成绩好不好,家长都会陪读。陪读意味着农民家庭必须抽出一个劳动力专门来陪伴子女学习,尤其是妈妈陪读,意味着作为壮劳力的年轻女性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降低了家庭经济收入,再加上在县城租房生活增加的消费支出,从而提高了家庭教育成本,降低了生活幸福感。因为陪读周期长,陪读妈妈在陪读结束后,由于脱离劳动力市场太久和年龄太大,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工作。《县乡的孩子们》指出,陪读不仅重塑了80后、90后农村女性的生命历程和生活轨迹,还重塑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结构,“走出家庭的女性因为子女的教育再一次被拉回家庭之中”。
几乎所有的陪读家庭都希望子女取得好成绩、考上好大学,陪读妈妈将注意力过度集中到孩子身上,不仅双方面临着较大的精神压力,亲子关系也相当紧张。陪读妈妈对生活大包大揽,孩子的唯一任务就是学习,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无法培养独立人格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2021年底,教育部等九部委联合印发《“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提出:“到2025年,县中整体办学水平显著提升,市域内县中和城区普通高中协调发展机制基本健全,统筹普通高中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推动全国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2%以上。”而在2022年的全国两会上,“加强县域普通高中建设”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县中如何“突围”?在《县中的孩子》中,林小英记下了一所县中——P中的成功案例。与大部分县中被“掐尖”的境况类似,2016年P县参加中考的学生,前100名里仅有15人能留在本校读高中。优质生源的流失,导致连年高考成绩不甚理想,趋势一旦形成,就很难逆转。但当地教育部门通过托管改革,让留在县中的老师和学生重拾信心。学校下放权力,激发老师的活力与创造力;压缩学校之前不规范的经费支出,整体提高老师的薪资标准,并为老师们提供免费早餐;引入小语种课程,让英语基础差的学生选择小语种参加高考。2022年P中高中部的本科上线率已达到63.2%,有效地促使P中回归了若干年前的荣耀。
在高考录取指标的裹挟下,很多县中更倾向于学习城里中学以及一线城市的教育改革经验,成为精英教育的追随者。但是“一所学校好,并不表明整个县域的教育好。精英教育是不太适合县域的”,作者林小英如是评价。
县域教育怎么办?出路在哪里?林小英在下乡调研中发现,很多深耕教育多年的当地校长和教师,早就试着放下以往评价制度中单纯对学习成绩的执念,转而真正思考如何为这些孩子们提供值得一生回想的学校教育体验:孩子们对文化课不感兴趣,他们就把兴趣类、动手类的课程开得有趣一些;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出卷子考试,让孩子们的成绩显得不那么难看;他们几乎熟悉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尽可能担负起一些外出务工的父母无法履行的责任……
县中的改革任重道远,但振兴的潜力依然蕴藏在教育的本质中。
[相关图书]
黄灯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黄灯在一所二本院校从教,长期的课堂教学以及课后的师生交流,使她成为这群学生成长变化的见证者。本书相当于她的教学札记,这里面有她15年一线教学经验的分享,对4500个学生的长期观察和长达10年的跟踪走访,也有两届班主任工作的总结思考,更有近100名学生的现身说法,是黄灯向读者描摹一群年轻人生活剪影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