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中国科学报
学术系统中的“自循环”评价虽无权威定义,但确是一种客观存在。
所谓“自循环”评价,泛指学术成果指标及其获得对象在学术评价中被“循环”使用的现象,即有关部门“自产”“自销”了某些学术成果指标和相应获得对象。此后,这些指标和对象又在其他相关学术评价中被采用。比如,“帽子”人才、项目、奖项、团队及基地等成果指标和获得对象大多出自各级管理部门,这些成果指标和获得对象又被各种学术评价项目大量采用,此类情况就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循环”评价成分。
放眼国内科教领域,各种貌似顶尖的科技成果指标及其获得者并不少见,但基础研究重大成果和解决“卡脖子”问题的核心成果却很短缺,这从侧面说明了“自循环”评价得出的“学术成果”并不能代表实际学术成果。“自循环”评价具有“自证”和自我强化评价结果的特性,对教育和科研等学术工作的不良导向不容小觑。
首先,学者的职业追求被异化为学术成果指标。“自循环”评价的一大特点是学术机构或个人一旦竞争得到了某项学术成果指标名额,机构或个人就可借此在之后的相关学术评价中屡屡“得分”。客观上,这些学术评价结果受制于前期的学术成果指标名额能否获得,因而得到学术成果指标名额对学术机构或个人的职业发展意义重大。
这种“上升”途径会使学者一旦得到某项学术成果指标名额,便会追求其他或更高级的成果指标名额。只有如此,机构或个人才能实现学术效益最大化。当学者把学术成果指标名额作为追求目标且止步于此时,许多本是“起点”的学术工作竟直接成为了“终点”。
其次,行政职务成为学者学术成功的重要“砝码”。毋庸讳言,不少学者之所以青睐行政职务,就源于这样更容易得到学术成果指标名额。现实情况也的确如此。究其原因,除了官员占得“人情世故”优势外,更主要原因在于“自循环”评价结果缺乏有效监督。因为“自循环”评价主体多为行政主管部门,其往往既是评价政策制定者,又是执行者。如此,学术系统内成员即使对评价结果有异议,一般也不敢提出申诉;而系统外人员对“自循环”评价结果本就没有多少发言权。而当“做官”成为年轻学者学术发展的首选条件时,便是对学术尊严的最大“讽刺”。
再次,学界成员被大范围卷入“自循环”评价活动中。有关部门越想展现政绩或业绩,就越要“制造”各种学术成果指标并广泛吸引相关人员参与指标名额竞争。而这类成果指标名额不仅关系到学术机构或个人的学术地位及荣誉,还可能影响到学术资源的分配。而且,由于“自循环”评价的特性,机构或个人一旦错过了一次指标名额就可能次次“落单”。
为此,只要有这类成果评价项目时,学术机构或个人即便手头正做着要紧工作也会立马放下去参评,因为谁也不想舍弃这样的机会。而参评者除了要准备大量的材料外,很多时候还需要花精力去“疏通”各种人脉关系。相比学术工作,学者将成果评价看得更重要,两者的因果关系被本末倒置。
最后,很可能导致“形式大于内容”的虚假繁荣。“自循环”评价的显著特点是学术成果指标由有关部门自己设定,有关部门又习惯给这些成果指标起一个“高大上”的名字。但不管这些名字有多好听,其终究只是有关部门想要开展工作的名称,相应指标名额的获得对象并不代表实际取得了指标名称成果。
然而在现实中,因为这些成果指标名额需要通过激烈竞争才能得到,同时它们又会被“循环”使用,一来二去,这些成果指标的获得对象就会被有意无意地认成实际成果获得者。由此,“自循环”评价“成果”琳琅满目,但许多只是“自娱自乐”。如果不加以警醒,甚至还自我陶醉,就会严重助长浮夸之风,污染学术生态。
综上,“自循环”评价带来的问题颇多。要想破解此局,严控行政权力对学术评价的过多干预最为重要。尤其对于学术成果的评价,评价主体要由“官评”为主转向由相关利益者共同参与。国家文件多次强调科技成果评价要“谁委托科研任务谁评价”“谁使用科研成果谁评价”,就是希望通过评价主体的适切,保障评出的科研成果“货真价实”。同理,眼下教学名师、优秀教学成果奖等指标成果获得者因偏离“教学”主题而受到公众质疑,如果能让学生、教师更多参与评价,相信结果会更令人信服。
从本质上说,减少不必要的学术评价是破解“自循环”评价问题的根本之道。学术系统是以高深知识为特征的自组织系统,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是为科教人员提供可以潜心学术工作的良好制度和环境。过多的学术评价不仅会扰乱学者的工作节奏,还可能被投机分子利用而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严重后果。不得不说,学术工作有其发展规律,优秀学术成果终究会因受众群体和学术同人的高度认可而脱颖而出。所以,有时“不评价”本身就是“评价”。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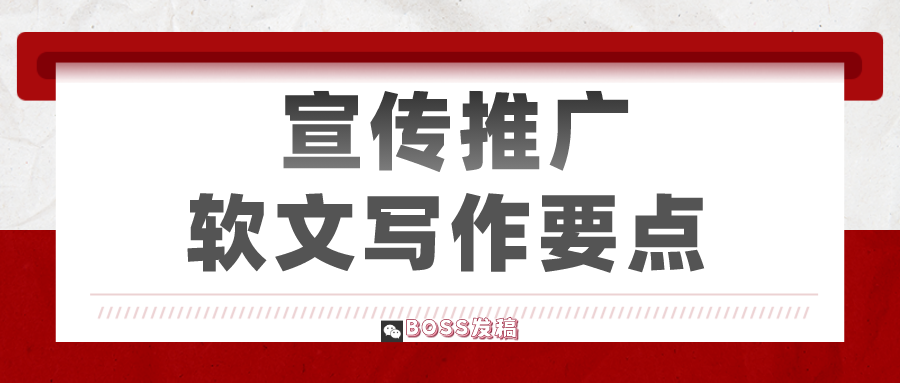
![[双语]例行记者会/Regular Press Conference(2024-1-9)]( https://img.jiaoyuzixun.net/upload/202401/1704853448_659dffc80a036.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