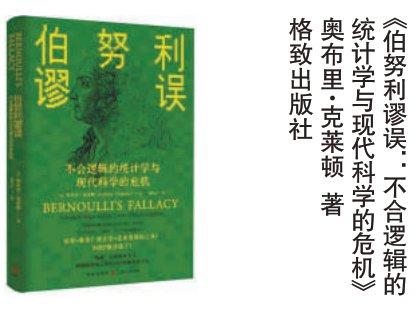刘易斯·芒福德
用W·H·奥登的话来说,我们生活的社会“对可衡量和可测量事物的研究有着狂热爱好”,我们很难想象还有其他什么替代方式能帮助我们处理现实世界。出于比较的目的,我们需要看另一种思维方式的例子。我们选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除了因为它们颂扬了一种非计量的或几乎可以说是反计量的方法,还因为它们绝佳地体现了我们原始的思维方式。这二人比我们更重视人类的理性(reason),但他们不相信我们的五感可以准确地衡量自然。因此,柏拉图写道,如果灵魂依赖感官获取信息,“它就会被肉体拉进变化无常的领域,并迷失方向,开始感到困惑和混乱”。
这两个希腊人将材料(data)分为两类,一类是我们可以十分确定的,另一类是我们永远不会确定的,此种分类标准与我们的不同。你我都会同意,日常经验的原始材料是变化无常的,而且我们的感官是不可靠的,但是我们相信,有这样一类事物,它们对我们来说是存在的,却不被这两位哲学家承认:这类事物足够均质,因而我们可以合理地对其进行测量,然后计算出平均值和中位数。至于说到进行此类测量时感官的可靠性,那我们就会明确指出在此可靠性基础上取得的诸多成就:动力织机、航天器、保险精算表,等等。这当然不是一个可靠的答案,因为我们的诸多成功可能是偶然的,可它却也是一个例证,说明了人类通常用来评估自己能力的方式:也就是问,什么可行,而什么不可行。为什么的确很聪明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会回避这类有益的可计量物?
这里至少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古人对量化测量的定义比我们的狭窄得多,而且常常为了一些更广泛适用的方法而拒绝这一概念。亚里士多德,这位被中世纪的欧洲等同于“哲学家”的人,发现相比于定量层面,在定性层面的描述与分析更有用。
我们会说重量、硬度、温度“和其他可感知的相互对立的性质”是可以量化的,但无论是在这些性质中还是在人类心智的本质中,这种可量化的特点都不是固有的。我们的儿童心理学家宣称,人类甚至在婴儿期就表现出了天生的计数离散实体的能力(三块饼干、六个球、八头猪),但是重量、硬度等,并不是作为离散实体的数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它们是状态,不是集合;而且更糟的是,它们通常处于流变之中。我们无法数清它们;我们必须用心智之眼去观察它们,通过命令(byfiat)去量化它们,然后计数单位数量。这很容易通过测量广延(extension)来完成。
对于祖先所犯的错误,我们总是有后见之明的优势,但要知道,可以用单位数量来衡量的东西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简单。
第二,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同,除了少数例外情况,我们都接受一种假设,即数学和物质世界是直接而紧密相关的。我们接受了一个看似不言自明的事实,即物理学这样一门与可感知的现实有关的科学,应当像数学那般极其精确。但这个命题并非不言自明;这是一个极不平凡的命题,许多圣贤都曾质疑过它。
超越用手指和脚趾计数水平的数学可能起源于测量的进步。那时的人们需要给粮食称重后销售,需要在底格里斯河和印度河之类河流旁的市场中记录羊和其它动物的数目,这些数目都很大,但之后,实际的测量和数学开始分化,并一直保持着这种分离。称重、计数和勘测都是世俗的活动,但数学被证明具有超然的性质,它令那些试图挣脱世俗束缚从而寻找真理的人陶醉。
柏拉图建议我们远离物质世界,因为物质世界是“流变之物”,他希望我们转向“永恒之物”。亚里士多德倾向于认为柏拉图主义缺乏实质内容。他相信感官材料,但对数学在解释这些材料方面有多大用处持怀疑态度。
科学(以及现代社会的许多其他特征)可以被定义为将具有柏拉图式精确性的数学应用于亚里士多德所谓未经雕饰的现实后得到的产物。但是抽象数学和实用计量学既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
记录表明,将抽象数学和实际测量相结合,之后又疏忽、忽略和遗忘,这种进步与倒退的循环是人类历史的常态。西方独特的智力成就是把数学和测量结合在一起,用其理解一种在感官上可知觉的现实,而西方人完成了一次信念的飞跃,认为这样的一种现实在时间和空间上是统一的,因此,也易于接受此类检验。
(作者为美国历史学家,芬兰科学院院士)